【艺术手册】“顽主”的“伤心”之处—王朔小说再解读

在当年的“王朔热”中,主流批评话语参与建构王朔的公众形象,将王朔建构为万人瞩目的“痞子英雄”。1王朔这一公众形象的确立,为告别社会主义时期的价值理想,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和个人自我观念开辟了道路。但某种意义上,王朔的“痞”恰恰是因为对社会主义时期价值理想及自身经验的珍视和缅怀。也就是说,王朔小说中“痞”的一面和伤心的一面本来具有同构关系,只有从后一面出发才能回答王朔的“痞”从何而来,但是,主流批评话语在参与建构王朔公众形象的过程中却遮蔽和剔除了这一面。因此,破除遮蔽王朔已久的这层“铁幕”,重新激活王朔小说提供的精神文化资源,就是题中之义。
当然,对于作为制度和理念的社会主义,王朔在小说中没有明确地描写。他对以往时代的缅怀,往往是隐喻性地表现在自己珍视的价值理想和经验情感层面;而对于社会主义的制度和理念,他的缅怀是模糊的,甚至是不自觉的。因此,王朔的这一面之所以被主流批评话语所遮蔽,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使人们在主观上“看不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王朔小说的表达方式使人们在客观上不容易看到。我们作为后来者,与以往主流意识形态拉开距离,因而就具有了揭示这另一面真相的可能性。
王朔公众形象简述
“痞子文学”成为王朔小说的标签,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王朔热”带来的结果。据论者考证,这个标签起源于电影界对王朔电影的评价,“痞子论”是宋崇的发明。2王朔后来回忆,“当时的北影厂长宋崇说我的东西是痞子写,痞子演,教育下一代新痞子。”3这个说法不胫而走,邵牧君在《王朔电影热缘何而起?》一文中说:“王朔电影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写中国当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青年阶层——痞子。”4
随着“痞子论”的确立,萧元在《王朔再批判》一书中以“痞子文学”为衡量标准划分王朔创作的几个阶段。书中认为,“痞子文学”这个概念可以分解为“写痞子的文学”和“痞子写的文学”两种含义:单纯“写痞子的文学”尚不足称“痞子文学”;只有对描写对象和内容,即对“‘痞子’的思想意识和行状持同情、欣赏、把玩和张扬态度的文学作品,才称得上‘痞子写的文学’”,才是真正的“痞子文学”。据此作者认为,王朔言情阶段的《空中小姐》《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是“痞子文学”的初级阶段,可称为“准痞子文学”;王朔调侃阶段的《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是“痞子文学”的高级阶段,是典型的“痞子文学”;而王朔以后写的《给我顶住》《动物凶猛》《你不是个俗人》仍算正宗的“痞子文学”,《许爷》《过把瘾就死》可算作“半痞子文学”5。这样的划分和命名显示出“痞子文学”这个标准的权威性和成规化。
在当年的“王朔热”中,经由对“痞子文学”的评定和论说,王朔的形象经历了从“痞子”到“英雄”的转变,“痞子英雄”最终成为王朔的公众形象。而在主流批评话语建构王朔这一公众形象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条脉络:由对“痞子文学”的评定和批评而到肯定“痞子文学”的真实性,从而确立起一个真(“真痞”)/假(“伪善”)二元对立的命题。依据这个命题,真实的是王朔式的“痞子行状”所符合的“自然人性”,虚假的是“左”的意识形态统治下“与人性作梗”的教条。例如,赵园当时认为,“王朔小说最严肃的旨趣也许就在揭穿成规惯例造成的虚伪,于规范破坏中发现‘真的人’”,从而“表达对于纯洁人性的怀念”6。而王蒙则直言:“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王朔自然也是应运而生。他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7金笛也强调,王朔“把矛头指向了已定型的与人性作梗的准则”,要调整文化秩序,就需要有“撕碎旧模式的勇气”8。
在“王朔热”中,随着这一真/假命题题域的扩张,更多内容被纳入到真实与虚假的范畴中,而判定真实/虚假的标准则大致相同,那就是对社会主义时期价值理想的批判和否定。也就是说,主流批评话语正是通过肯定王朔写作对于解构社会主义时期价值理想的意义,通过肯定王朔式“痞子行状”包含的种种“颠覆性”因素,才将王朔塑造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开路的“痞子英雄”。
王朔这一公众形象的确立,同时也为一种原子化的个人观念——放逐精神理想,丧失对社会、他人的责任感,以自我为中心,释放物质欲望,沉迷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将世俗幸福和个人功利作为唯一的人生目标等——提供合法性,为这种观念的确立开辟了道路。
但是,王朔这一公众形象却遮蔽和剔除了其小说中深刻的心理创伤,说得通俗点,遮蔽和剔除了王朔伤心的一面。因此,要破除主流批评话语对王朔的遮蔽,首先就要解读王朔相关作品,将这一面重新呈现出来,然后再回答这一面与王朔的“痞”究竟是何种关系。
伤心的王朔
陈思和曾在《黑色的颓废》一文中谈到,“王朔笔下的主人公只有一个肉身”,其通常是身兼叙述人和主角的“我”,也可化名为不同的人物,“他们有着十分相似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做着同样的梦,依循着同样的人生原则。”9据此,文章认为早在《空中小姐》中王朔就交代了“这个身份固定的叙事人的真正来历”:他是个退伍军人,1970年代参军,“其军人模式是按照那个时代的理想塑造的”,“可是在他离开军队时,中国社会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商品经济冲击了传统的文化规范”;他发现自己无法适应新的现实世界,只能痛心疾首地注视着自己“怎样一步步堕落下去”,但他同时还企图自救。小说《空中小姐》中叙事人与阿眉的梦中重逢,就是一种“自救”的企图和努力。文章认为:
这个梦包含了“王朔式英雄”的性格发展的起点。这个梦象以后随着主人公“我”的堕落一步步淡化,甚至远离他,可是在王朔的小说里它成了一种神秘的力量,时隐时显地浮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启迪着“我”久被封藏的良知。以后,王朔的小说里总是出现一个纯情女孩的意象,千篇一律,她是王眉生命的延续,也是那个梦想投射在尘世的幻影。她在“王朔式英雄”的心目中是绝对神圣的,尽管这位主人公在人生道路上不断滑向商品社会的污浊层面,也尽管这个梦象对他越来越模糊,甚至难以记忆。10
的确,王朔作品中有不少纯情小说,大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叙述人不管是否和王朔共享曾经的1970年代军人身份,与作者之间都没有明显的距离,因此这个叙述人常常是作者的代言人。而在叙述人的经历中,总会出现一个纯情女子形象,这个形象“启迪着‘我’久被封藏的良知”:其或者与“我”有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或者与“我”短暂相逢惺惺相惜,但最终离“我”远去,随之而来的则是“我”深切地追念和不可复得的伤心。
这些讲述男女纯情故事、抒发伤心体验的小说,感动了千千万万青年读者,是“王朔热”形成的重要动力,但是其与“痞子文学”批评话语逻辑的抵牾却往往被忽视。这些小说主要有《空中小姐》《永失我爱》《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过把瘾就死》《动物凶猛》等。下面对这些作品作一些分析。
《空中小姐》讲述“我”与阿眉的感情故事。叙述人与王朔一样曾经具有1970年代军人身份。如小说中所言,“我”原本是“作为最优秀的青年被送入部队的,如今却成了生活的迟到者”,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胖子”。而阿眉如今则是一个令无数人羡慕的空中小姐。“我”和阿眉的处境相差甚远,爱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阿眉崇拜那个过去的“我”,即1970年代那个英姿飒爽的海军战士。这种崇拜可以让阿眉接受“我”现在的一切,但是却不能消除“我”对自身处境的敏感和自尊心受到的伤害。昔日理想的失落、现实的无可适从、与阿眉身份地位的差距,迫使我最终忍痛提出分手。当阿眉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后,“我”得知阿眉对“我”的爱始终如一。
这篇小说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笔触很少进入阿眉的内心世界,因而阿眉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而只是“我”主观心理的投射。所以,阿眉对“我”的爱只是“我”往昔英武形象和军人身份的见证。而1970年代的军人身份记载着社会主义时期的价值理想,因此,阿眉这个纯情少女形象正是这身份记忆和价值理想的隐喻。“我”对阿眉的苦苦追恋,体现的是“我”对1970年代军人身份的认同和对那个年代价值理想的缅怀。小说最后,阿眉来到“我”的梦中,把她全部的情感和力量赠予“我”,让“我”获得新生。实际上,这恰恰彰显出“我”对于她所承载的身份记忆和价值理想的难以割舍之情:
阿眉来了!
冰清玉洁,熠熠生辉。
她拥抱了我,用空前、超人的力量拥抱了我,将我溺入温暖的海洋中。她用岩浆般沸腾的全部热情,挤压着、置换着我体内的沉淀污垢物;用她那晶莹清冽的全副激情,将我身心内外冲刷得清清白白。我在她的拥抱,治疗下心跳、虚弱、昏厥,她的动作温柔了。蓦地,我感到倾注,像九溪山泉那样汩汩地、无孔不入地倾注,从她的心里。流速愈来愈快,温度愈来愈高,我简直被灼疼了。天哪!这是她贮存的全部鲜血、体液,是她积蓄的,用来燃烧青春年华的能量,她再发出耀眼的光亮,就无偿、慷慨、倾其全体地赠予了我。我感到一个人全部情感和力量的潜入,感到自己在复苏,在长大。我像一支火炬熊熊燃烧起来。而阿眉,却像一盏熬尽了油的小灯,渐渐黯淡下去,微弱下去。我清晰地看到她泪流满面却是微笑着,幻作一个天蓝的影像,轻松地、一无所有地飘飘升飞。11
陈思和认为,这个梦虽然体现了叙述人自救的企图,但是“没有什么新意”:“在寓意上它是以一个人的死来更新另一个人的生命,也没有摆脱传统英雄主题的理想色彩;它的内容写死者用鲜血、体液倾注生者的肉身,更未摆脱浪漫主义爱情永恒的含义。”12的确,在当年的“王朔热”中,这篇小说对以往时代价值理想和身份记忆的追恋,往往被批判和否定“乌托邦时代”的人们视为落入了传统的窠臼。《十作家批判》一书“给王朔的所有中短篇小说排名次”时,把这篇小说排在“中等偏下”。13《王朔再批判》一书认为这篇小说不过王朔“痞子文学”的初级阶段。14《王朔批判》一书则认为,这篇小说虽然“完成了一个曲折故事的真实叙述”,但还只是体现了后来小说所写的那种“痞子”、“顽主”的某些因素,不过是王朔“向自己的感觉靠近,唤醒自己潜在话语”的过渡。15
当时主流批评话语讨论这篇小说的重点是关注它在多大程度上“痞”,或者多大程度上不“痞”。这种归类式的思维首先是坚持某一种评价标准,然后用所持标准来衡量这篇小说。在这种封闭的评判方式下,只有排除那些事关社会主义时期价值理想和作者身份认同以及心理创伤的内容,这篇小说才能被赋予意义。由此也可见出“痞子英雄”这一公众形象对于王朔另一面的遮蔽。
《永失我爱》与《空中小姐》有几分相似,讲述“我”与纯情女子石静的生离死别。小说中,“我”是建筑工地的一位卡车司机,由于一次见义勇为、扑火救人的高尚行为,“我”患上了不治之症。为了不拖累未婚妻石静,“我”向她隐瞒了病情并故意制造自己负心的假象,终于迫使她和“我”分手。最后,石静知道了真相,在她的泪眼注视中,“我”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这篇小说中,纯情女子离“我”远去的原因不再是她的牺牲而是“我”的罹难。小说借此深切缅怀以往时代所倡导的高尚无私、纯洁坚贞的爱情关系;与此同时,通过描写工友们对待“我”和石静婚变的态度,呈现了对于工人阶级身份的认同。
小说这样描写闻讯而来的工友对“我”的劝告:
“别喝了!你胡说什么?你哪有什么‘情儿’,我天天和你在一起还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
“我凭什么就不能有‘情儿’?”我翻着白眼拿腔拿调儿地说,“别太瞧不起工人,工人怎么啦,工人勾搭起人来也有手腕着呐。”
“何雷,”董延平双肘压在桌上,充满感情地说,“咱是老粗但不是流氓对不对?见异思迁吃里扒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都是知识分子好干的事儿。咱们,你也不是一向顶瞧不上?”
⋯⋯⋯⋯
“何雷,咱祖祖辈辈可没出过流氓。”16
这番劝告呈现出工人群体对于人际关系的理解:一位工友在爱情婚姻上的背信弃义,并不仅是你自己的事情,不仅有损你的人格,而且损害整个工人队伍的形象和荣誉。所以,董延平劝说“我”的方式不是说“我”的负心怎么对不起石静,而是说这不符合咱们工人阶级的原则——“咱是老粗但不是流氓”。这传达出的无疑是社会主义时期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小说中进一步描写当“我”不听劝告一意孤行时,工地上的同事们表现出来的义愤、轻蔑、鄙夷,就连食堂卖饭的胖姑娘都对“我”满面冰霜,饭菜也给得比往常少得多。而且,工地医务室大夫吴姗为了帮“我”实现不拖累石静的目的而甘愿扮演“第三者”,同样遭到激愤的同事们的一致谴责。这些或许会被某些自由主义者指责为干涉私人生活,妨碍“消极自由”,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专制吧。因此,小说表达的依然是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情感经验、身份认同和价值理想的缅怀以及对其不可复得的感伤。小说结尾这样描写石静来到病房探望“我”的情景:
石静向我移步走来,她晶莹透明,肤若蝉翼,她的眼睛像浸于一缸清水的雨花石,纯净滑润⋯⋯
我面无表情地望着她——我已经无法作出任何表示了,连笑一下也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种东西还是自由的,它从我眼中流出,淌过我毫无知觉的面颊,点点滴在那只向我伸来的美丽的手⋯⋯17
石静“那只向我伸来的美丽的手”象征的是纯洁无私、高尚坚贞的爱情关系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但如今面对其召唤,“我”已无法作出回应,“我”正在离它远去。这当是小说题目“永失我爱”的深刻寓意。而这种寓意与“王朔热”中真/假命题存在明显的抵牾:在真/假命题中,“痞子行状”被说成是符合真实人性的,而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则是虚假的,被认为是王朔所要消解和颠覆的东西。主流批评话语与小说文本之间的这种抵牾,彰显出王朔公众形象建构过程中对异质性情感和精神资源的排斥与剔除。
与以上两部作品相比,《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更多地展示了王朔式的“痞子行状”,根据其改编的电影当是“痞子论”的重要依据,但是同样被当时论者划定为“准痞子文学”,这或许是因为其一方面展示了“痞子”的生存状况,另一方面表达了对这种状况的痛切反思。这部小说分为上下两篇,分别塑造了两个纯情女子形象:吴迪和胡亦。这两个形象之间有密切关联,共同构成改革初期某种精神症状的隐喻。
小说中,叙述人“我”原本是一个组织卖淫再冒充警察敲诈勒索的“痞子”。由于对纯洁的女大学生吴迪的勾引和抛弃造成她的沉沦和自杀,“我”极度伤心愧疚。这使“我”出狱后又充当了保护、救助纯情女子胡亦,惩治流氓的英雄角色。其中,令人深思的是,“我”在勾引吴迪的过程中,对自己恶劣品行的介绍,句句都是实情,但是在吴迪看来,却是一种好玩和有趣。这是“传统道德受到普遍蔑视的时代”给吴迪造成的深刻影响,“我”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才达到了勾引她的目的,而这也最终导致了吴迪发现真相后的悲惨结局。
胡亦是吴迪这一形象的延续,她也是有反叛意识的女大学生,由于鄙视传统社会规范和中国式的“假深沉”,故意作出放荡形骸的样子,后被两个自称作家的流氓诱奸,只是在“我”的救助下才没有走向沉沦和堕落。在胡亦与那两个流氓的接触过程中,“我”一直告诫她不要上当受骗,但“我”的话都被她视为“乏味”、“假深沉”。她用与“我”当初对吴迪说过的一模一样的话来嘲笑“我”。这当然是作者的有意设置,意在形成强烈的讽刺效果。而且在“我”与胡亦的交往中,也设置了多处与“我”和吴迪交往时相同的场景和对话。正是通过这样的设置,作品表达了对“痞子行状”和改革初期社会精神症状的质疑和反思。
《橡皮人》延续了上述社会反思的逻辑。小说以叙述人“我”和一帮同伙在某经济特区非法倒卖汽车电器为线索,表现这个群体生活的堕落和人际关系的丑恶。但是,这里仍然出现了一位纯情女子的形象,她叫张璐,是女兵,革命军人的女儿。虽然“我”们一帮男女同伙之间性关系非常混乱,但张璐是“我”决不忍心染指的,她的纯洁使“我”不会产生任何非分之想,就连同伙张燕生都严肃地告诫“我”:“别碰她。”张璐使“我”和张燕生想起了美好的童年往事,也使“我”当晚做了一个恶梦:“我”处在“万木凋零”、“虎狼相伴”的荒原,近在咫尺有一“锦绣之地”,但随之地裂,锦绣之地渐渐远去,可望而不可即,“我在荒原哭泣”,随后变成了啮食生肉的非人。小说中,这种强烈的异化与非人化的感觉经常伴随着“我”。最后“我”变成了橡皮人,同时又见到已经结婚的张璐。可见,张璐这一纯情少女形象寄托了“我”的某种渐渐远去但又难以割舍的理想和记忆,这使得“我”对当前龌龊的生活状态产生强烈的质疑和痛切的反思。
如果说《空中小姐》和《橡皮人》分别代表了“追念过去”和“反思现状”这两种叙事逻辑,那么,在《过把瘾就死》中这两种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就交汇到了一起。这篇小说讲述了“我”(方言)与纯情女子杜梅从恋爱结婚到婚姻破裂的情感经历。对于这场婚姻的破裂,有两个事件特别关键。第一个是:一天晚饭后杜梅与方言发生争吵,杜梅说了一番挖苦方言的气话,深深刺痛了方言。在争吵暂时平息后,小说中这样描写方言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创伤:
实际上我最激烈的思想活动没有告诉杜梅。那种令我齿冷令我感到受到严重伤害的感觉一直带到我们上床睡觉,甚至连做爱也没有使我忘掉它。尽管我知道她是无心的,但我也不能原谅她。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原谅过任何人。我可以容忍别人对我的谩骂、攻讦,容忍别人怀疑我的品质,哪怕贬低我的人格,但我决不容忍别人对我能力的怀疑!此辈我定要追至天涯海角,竟我一生予以报复。我活着、所作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些曾经小觑过我的人逐一踩在脚下!18
这样的心理创伤显然超出了家庭争吵的范围。实际上,不是杜梅的挖苦给方言造成这种心理创伤,而是杜梅的挖苦击中了这种心理创伤。这心理创伤构成了方言与杜梅矛盾激化的潜在心理依据。第二个事件由肖超英、潘佑军在方言家喝酒引起。他们三人本是一起长大的哥们,一起参军的战友,方言和潘佑军复员回到北京,而肖超英留在部队当了干部,他回京探亲,三人聚在方言家喝酒。三人深情地追忆昔日的部队生活及在全军比武中各自的英勇表现,酒从中午喝到下午、喝到天黑。杜梅下班回家后,实在忍无可忍,终于下了逐客令,这让方言对她大打出手。小说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
这时,我脑袋忽地一热,像什么成块成吨的东西忽然迸碎了,衬衣的扣子也绷掉了,站起转身抡圆了就是一个大耳光结结实实贴在杜梅的脸蛋上。随即破口大骂:
“你也太不懂事了!轰他妈我们哥们儿。我们多少年没见了?告诉你要滚你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没你呢!”19
正是这次轩然大波将方言和杜梅的感情推向了冰点。
这两件事有着内在联系。先就第二件事来说,方言之所以瞬间失控大打出手,是因为杜梅的逐客令冒犯和嘲弄了方言的身份认同和记忆。上引杜梅下逐客令后“我”脑袋里忽然迸碎的“成块成吨的东西”,正是方言他们三人深情追忆的1970年代的军人身份,这种记忆是方言深埋心底、非常珍视的。如果仅仅把他的粗暴归因为在哥们面前尽失颜面,就很难解释后面方言一直未对自己的粗暴感到愧疚,也从未向杜梅道歉的表现。这种似乎不合常理的情节安排暴露了作者的无意识:方言的行为是正当的,方言珍视的东西不容冒犯!这彰显出作者对方言行为的高度认同,方言和作者共享着同样的军人身份记忆和自我意识。
明了上述心理逻辑后,就不难理解第一件事中方言(作者)的心理创伤。方言珍视的军人身份记载着昔日的英雄本色和价值理想,但因时代转变,这些变得一文不值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言们(作者)是时代转变的弃儿。正是这种强烈的被遗弃感造成的心理创伤,使他对自己如今的处境特别敏感,一旦遭到小觑,就激起他强烈的甚至恶毒的报复心理,哪怕是对于杜梅。而他之所以可以容忍别人对他的谩骂、攻讦,对他品质的怀疑、人格的贬低,是因为他不接受当今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是因为他的叛逆。而这种叛逆心理和报复心理具有同构性,都是时代转变造成的心理创伤的反应。
如果说上述内容是《空中小姐》代表的叙事逻辑和心理逻辑的延伸,那么通过方言和杜梅的婚姻关系,这篇小说同时还补全了《橡皮人》中叙述人“被遗弃荒原”的荒诞处境背后的心理逻辑。小说开头说:“杜梅就像一件兵器,一柄关羽关老爷手中的那种极为华丽锋利无比的大刀。”20杜梅性格的锋利体现在她对爱情的偏执乃至疯狂的追求上。她的柔情蜜意背后是敏感多疑、刚强固执、歇斯底里。这种杜梅式的爱情有幼时家庭变故的影响——其父因婚外恋杀死其母,但更是时代转变的产物。随着时代转变,理想主义在社会领域退场,以往时代的理想和激情转移到了个人爱情领域,铸就了杜梅式的爱情——理想主义的爱情。而对于方言来说,他的问题是并未实现这样的转移,他无法在柔情蜜意的家庭生活中安顿身心。他在与杜梅的激烈争吵中道出了心里话:“我那么在乎每天下班回来能捏着小酒盅啃猪蹄子你坐在旁边含情脉脉地望着我?我那么在乎冬穿皮衣夏穿纱那么在乎被窝里有个热身子?”21这表达出方言自我意识中对庸常生活的蔑视,这同样是时代转变造成的心理创伤的反应。对家庭生活的不同态度导致婚姻破裂。婚姻破裂对于方言来说是生活更加无聊,是对生活更加没有感觉,而对于把理想和激情都押在爱情上的杜梅来说,则意味着灭顶之灾。
小说结尾,一个午夜,方言、潘佑军等人在偏僻的马路上遇见杜梅一个人骑车狂奔,当方言等人拦住她的时候,只见她“头发披散、眼露凶光,像个巨大凶猛的猩猩”22。当方言等人抬她上车时,她的拼力挣扎、对众人的攻击、令人“毛骨悚然”的哀号证明她精神的疯狂状态,而且醒来竟不自知。正是这一夜方言发现自己是“那么爱她”。小说中这样写道:
那天夜里,我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那种巨大的、澎湃的、无可比拟的、难以形容的、过去我从来不会相信会发生在人类之间的激情。
这情感的力量击垮了我,摧毁了我,使我彻底崩溃了。我不要柔情、不要暖意,我只要一种锋利的、飞快的、重的东西把我切碎,剁成肉酱,让我痛入骨髓!23
当时崔健的摇滚歌曲里有一句流行歌词:“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对崔健赞赏有加的王朔在这里表达了同样的感受。这种感受是时代转变造成的精神症状。杜梅由全部生命激情铸就的爱情之刀,让“我”猛然有了存在的感觉,“我”愿被剁成肉酱痛入骨髓,因为这可以让我不再是没有感觉的“橡皮人”。以上当是“过把瘾就死”这个小说名字的由来,也是《橡皮人》中未被言明的心理逻辑。
通过对王朔纯情小说进行文本细读,我们呈现出了“伤心的王朔”的基本面目。概括地说即:第一,对社会主义时期价值理想和身份记忆的难以割舍和不可复得的伤心;第二,对“痞子”的生存状态和改革初期社会精神症状的痛切反思。在此基础上,就可进一步讨论:王朔的“痞”到底从何而来?对于这个问题,上述心理逻辑已经提供了解答的线索,而《动物凶猛》则正面作出了回答。
《动物凶猛》的秘密:王朔的“痞”从何而来
《动物凶猛》发表于1991年,是王朔创作鼎盛期的总结性作品,是王朔写得最为深情的一篇,也最被他自己看重。小说开头这样写道:
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自我慰藉。
我很小便离开了出生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作故乡。这个城市一切都是在迅速变化着——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它已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崭新、按我们的标准挺时髦的城市。
没有遗迹,一切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24
以上文字,首先把乡村(故乡)与城市(故乡)这种空间的差别转化成时间的差距。因乡村(故乡)变化缓慢,所以可充当以往时代经验和记忆的载体,而城市(故乡)却没有这样的可能。作者自小生活的这个大城市已完全改观,以往时代“没有遗迹,一切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自然,“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也就无从寄托。那么,“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是什么呢?接下来作者写道:
我在人前塑造了一个清楚的形象,这形象连我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不论人们喜爱还是憎恶都正中我的下怀。如果说开初还多少是个自然的形象,那么在最终确立它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多种复杂心态的左右。我可以无视憎恶者的发作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了醋。
我想我应该老实一点。25
这里作者对自己的公众形象直接进行审视。从个人名利的角度讲,这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公众形象“连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但是,自己知道它并不是自然的,在确立它的过程中,自己“受到了多种复杂心态的左右”。“多种复杂心态”当中自然包含着迎合主流话语建立自己社会名望的动机。而“为了不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作者坦陈这个公众形象违背自己的初衷和本意,它就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了醋”。所以,作者这一次要“老实”地讲一些隐藏在内心当中真实的东西。
接下来,作者深情地讲述了“我”青少年时代和米兰之间的感情故事。故事发生在1970年代中期的北京,很多人认为那是个“专制”的时代,但这个故事却给孩子们打开了一片“自由的天地”:“我”们不必再遭受父母和老师的监管,可以自由自在,无所顾忌。这为“我”和米兰的结识提供了机会。“我”在一次溜门撬锁的游戏中,潜入米兰的闺房,发现了她的照片;后来和一群雄踞街头的少男少女被解往派出所时见到了米兰。小说这样描写两次相见的感受:“那个黄昏,我已然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正常反应,视野有多大,她的形象便有多大;想象力有多丰富,她的神情就有多少种暗示。”26“但我看她的第二眼,这个活生生的、或者不妨说是热腾腾的艳丽形象便彻底笼罩了我,犹如阳光使万物呈现色彩。”27
“我”自见到米兰的照片就深深地迷恋上她,日复一日地守候在她家楼房前,热切期待着她的出现,甚至为自己被她牢牢抓住无法解脱而感到恐惧。而且,和米兰结识后,会因渴望见到她而失去正常的感知,出现种种难堪症状。但只要一见到米兰,那些症状就都消失了。“我”对米兰的迷恋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当和米兰单独相处时,“我”又老实又听话,没有任何“痞子”相,即使有时故意吹嘘自己干过的荒唐事,也是为博得她的青睐。“我”甚至显得可怜巴巴,不敢说话,不敢正眼看她。在她面前,“我”自甘于一种弱小的从属地位,渴望获得她的关爱。
和米兰一直保持这样的关系,自然是“我”梦寐以求的心愿,但情况发生了逆转。当“我”为了炫耀而把米兰介绍给高晋他们之后,“我”逐渐发现米兰和高晋的关系越来越不一般,米兰正逐渐离“我”远去。这时,一种痛苦的被遗弃感改变了“我”对她原来的美好印象:
我对米兰说话的措辞愈来愈尖刻⋯⋯她在我眼里再也没有当初那种光彩照人的丰姿⋯⋯一言以蔽之:纯粹一副贱相!
我再也不能容忍这个丑陋、下流的女人⋯⋯28
这里对米兰的贬斥与前面的礼赞形成鲜明反差。痛苦的被遗弃感使得“我”一下子变得“痞”态百出,挖空心思想出种种“痞”方对待她。“我”对米兰的这种惊人变化,实际上正是因为“我”对她的深切眷恋和难以割舍。“我”的“痞”是遭她遗弃之后极度伤心的非正常反应。当“我”最终意识到自己被彻底遗弃时,“我”强暴和亵渎了米兰——而这,恰恰意味着永远的失去了她。小说结尾写道:“我抽抽嗒嗒地哭了,边游边绝望地无声饮泣。”
小说为我们编织了这样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但有意味的是,小说一边讲述这个故事,一边又解构这个故事:
我发现我又在虚构了。开篇时我曾发誓要老实地述说这个故事,还其真相。
可我还是步入了编织和合理推导的惯性运行。
背叛我的就是我的记忆。
我和米兰从来就没熟过!29
小说中这种解构故事的文字反复出现,不断打断故事进程,但作者又按照原有逻辑把故事强行讲完。如果不把这仅看作是卖弄“现代派”的叙事技巧,而是另有深意,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其实是暗示读者:“我”和米兰的故事并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米兰这个纯情女子是作者珍视的以往时期价值理想的隐喻。小说中还有一位放荡的女子于北蓓,她总是在米兰不在场的时候出现,在她和米兰身上,作者寄托了不同的感情和想象。于北蓓代表着身体欲望的一面,她是使“我”堕入欲望陷阱的诱因,而“我”对米兰的迷恋则没有什么身体欲望搀杂其中:“那时,我真的把自己想成是她的弟弟,和她同居一室,我向往那种纯洁、亲密无间的天然关系,我幻想种种嬉戏、撒娇和彼此依恋、关怀的场面。”30因此,米兰承载着作者青少年时代纯真的理想和珍视的价值,这正是小说开头所说的“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
这样,王朔深情讲述的这个“我”和米兰的感情故事就揭示出王朔的“痞”究竟从何而来:因为时代的转变,社会主义时期的价值理想猝然远去,遗弃了王朔,所以他才示以种种“痞”相。也就是说,王朔的“痞子文学”对社会主义时期价值理想的种种嘲讽和诋毁,正是因为时代转变自己被这价值理想遗弃后极度伤心的非正常反应。这反证了王朔对以往价值理想的难以割舍。因此,当亵渎了这价值理想之后,他就像亵渎了米兰的“我”一样陷入无限的空虚、麻木与绝望之中,陷入方言们共享的“橡皮人”一样的荒诞处境之中。这正是《动物凶猛》要揭示的秘密,也是王朔要老老实实讲这个故事的真意所在。
在《我是王朔》一书中,王朔曾深情地说道:
我认识到理想主义的问题。但咱们这一代人,说实话,哪能没有理想啊?我对真正的理想是珍视的,我不允许别人利用这些东西来诱惑我。⋯⋯人类有时需要激情,为某种东西献身是很大的东西,我并不缺少这种东西。但这种东西必须出自内心。我看到的却是这些美好的东西被种种的学说被资产阶级自由化,被亡我之心不死的别有用心的人给毁地差不多了。
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割舍的。《动物凶猛》就流露出我对那种已经彻底消失的东西的一种缅怀,有非常强烈的怀旧情绪。
我第一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他写出了我们与环境之间难于割舍的,血肉相联的关系,可是现在又有了矛盾。⋯⋯那种环境毕竟给了你很多东西。所以看苏联这种情况,我特矛盾。我们青年时代的理想和激情都和那种环境息息相关,它一直伴随着你的生命。
说我的作品痞,这是总的错了。其实我的作品不痞。虽然其中有油滑调。31
这些内心表白,袒露了王朔对社会主义时期理想和激情的珍视与缅怀。王朔同时还说明了理想和激情发自内心与以之蛊惑别人的区别。这或许正是《动物凶猛》中“我”经由自己的探索而迷恋上米兰的原因——米兰代表的价值理想正是出自他自己的内心。王朔的以上表白和言说是在1992年5月,非常接近作品创作的时间,与作品中所抒写的思想内容正可相互印证。
这显然可以见出,王朔并非如当时主流批评话语所说的:是因为看透了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欺骗性和伪善本质,才用种种痞的方式嘲讽它,诋毁它。正好相反,王朔的叛逆、他的“痞子文学”恰恰源自他对往昔时代价值理想不可复得的伤心。也就是说,王朔“痞”的一面和伤心的一面具有同构关系,是那个年代王朔们同一心理结构的两个方面。
这也显然见出,当年主流批评话语在建构王朔公众形象的过程中,如何对王朔小说提供的经验进行选择、剔除和删改,如何操控着王朔文本意义的生产,如何将社会主义时期的价值理想和经验记忆毫无反思不由分说地清除出去,从而构造出一套关于个人、自由、解放、欲望的神话,向全球资本主义顶礼膜拜的神话。
1 “王朔热”前后有三次,第一次是由1988年王朔的电影热引发的关注;第二次是90年代初,由王朔参加编创的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陆续上映产生轰动效应,再加之他个人文集的出版,引发社会对他创作(包括影视创作)的全面关注,这期间王朔还成立了“海马影视创作中心”、“时事文化咨询公司”,更加助长了其声势;第三次由1999年末王朔挑战金庸引起,广大“金庸迷”群情激愤,各媒体也追踪报道,其中网络得风气之先,形势很快发展为“王朔批金庸,大家批王朔”,金庸的支持者和王朔的支持者之间展开激烈论战,但王朔一边明显占劣势。这一讨论并没持续多久,也没产生多大影响,可看作“王朔热”余绪。本文中“王朔热”主要指前两次。
2 黄平:《没有笑声的文学史——以王朔为中心》,《文艺争鸣》,2014年第4期。
3 王朔:《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天涯》,2000年第2期。
4 邵牧君:《王朔电影热缘何而起?》,《中国电影报》,1989年3月25日
5 萧元:《王朔再批判》,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70-71页。
6 赵园:《“难见真的人!”——试说〈轮回〉改编原作的得失》,《电影艺术》,1989年第5期。
7 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8 金笛:《何必“谈朔色变”》,《中国青年报》,1993年2月13日。
9 陈思和:《黑色的颓废——读王朔小说的札记》,《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5期。
10 同上。
11 《王朔文集》(1),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85-86页。
12 陈思和:《黑色的颓废——读王朔小说的札记》。
13 朱大可等:《十作家批判》,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6页。
14 萧元:《王朔再批判》,第71页。
15 张德祥、金惠敏:《王朔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5-46页。
16 《王朔文集》(3),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233页。
17 同上,第239页。
18 王朔:《王朔文集》(4),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386页。
19 同上,第395页。
20 同上,第333页。
21 同上,第420页。
22 同上,第437页。
23 同上,第439页。
24 同上,第248页。
25 同上,第248—249页。
26 同上,第255页。
27 同上,第273页。
28 同上,第316、317页。
29 同上,第321、322页。
30 同上,第289页。
31 王朔等:《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第80、34、76、27页。
在当年的“王朔热”中,主流批评话语参与建构王朔的公众形象,将王朔建构为万人瞩目的“痞子英雄”。1王朔这一公众形象的确立,为告别社会主义时期的价值理想,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和个人自我观念开辟了道路。但某种意义上,王朔的“痞”恰恰是因为对社会主义时期价值理想及自身经验的珍视和缅怀。也就是说,王朔小说中“痞”的一面和伤心的一面本来具有同构关系,只有从后一面出发才能回答王朔的“痞”从何而来,但是,主流批评话语在参与建构王朔公众形象的过程中却遮蔽和剔除了这一面。因此,破除遮蔽王朔已久的这层“铁幕”,重新激活王朔小说提供的精神文化资源,就是题中之义。
当然,对于作为制度和理念的社会主义,王朔在小说中没有明确地描写。他对以往时代的缅怀,往往是隐喻性地表现在自己珍视的价值理想和经验情感层面;而对于社会主义的制度和理念,他的缅怀是模糊的,甚至是不自觉的。因此,王朔的这一面之所以被主流批评话语所遮蔽,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使人们在主观上“看不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王朔小说的表达方式使人们在客观上不容易看到。我们作为后来者,与以往主流意识形态拉开距离,因而就具有了揭示这另一面真相的可能性。

王朔公众形象简述
“痞子文学”成为王朔小说的标签,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王朔热”带来的结果。据论者考证,这个标签起源于电影界对王朔电影的评价,“痞子论”是宋崇的发明。2王朔后来回忆,“当时的北影厂长宋崇说我的东西是痞子写,痞子演,教育下一代新痞子。”3这个说法不胫而走,邵牧君在《王朔电影热缘何而起?》一文中说:“王朔电影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写中国当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青年阶层——痞子。”4
随着“痞子论”的确立,萧元在《王朔再批判》一书中以“痞子文学”为衡量标准划分王朔创作的几个阶段。书中认为,“痞子文学”这个概念可以分解为“写痞子的文学”和“痞子写的文学”两种含义:单纯“写痞子的文学”尚不足称“痞子文学”;只有对描写对象和内容,即对“‘痞子’的思想意识和行状持同情、欣赏、把玩和张扬态度的文学作品,才称得上‘痞子写的文学’”,才是真正的“痞子文学”。据此作者认为,王朔言情阶段的《空中小姐》《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是“痞子文学”的初级阶段,可称为“准痞子文学”;王朔调侃阶段的《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是“痞子文学”的高级阶段,是典型的“痞子文学”;而王朔以后写的《给我顶住》《动物凶猛》《你不是个俗人》仍算正宗的“痞子文学”,《许爷》《过把瘾就死》可算作“半痞子文学”5。这样的划分和命名显示出“痞子文学”这个标准的权威性和成规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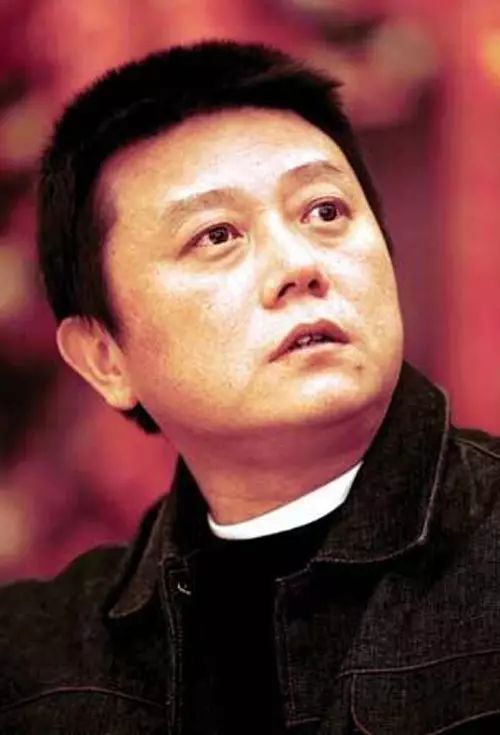
在当年的“王朔热”中,经由对“痞子文学”的评定和论说,王朔的形象经历了从“痞子”到“英雄”的转变,“痞子英雄”最终成为王朔的公众形象。而在主流批评话语建构王朔这一公众形象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条脉络:由对“痞子文学”的评定和批评而到肯定“痞子文学”的真实性,从而确立起一个真(“真痞”)/假(“伪善”)二元对立的命题。依据这个命题,真实的是王朔式的“痞子行状”所符合的“自然人性”,虚假的是“左”的意识形态统治下“与人性作梗”的教条。例如,赵园当时认为,“王朔小说最严肃的旨趣也许就在揭穿成规惯例造成的虚伪,于规范破坏中发现‘真的人’”,从而“表达对于纯洁人性的怀念”6。而王蒙则直言:“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王朔自然也是应运而生。他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7金笛也强调,王朔“把矛头指向了已定型的与人性作梗的准则”,要调整文化秩序,就需要有“撕碎旧模式的勇气”8。
在“王朔热”中,随着这一真/假命题题域的扩张,更多内容被纳入到真实与虚假的范畴中,而判定真实/虚假的标准则大致相同,那就是对社会主义时期价值理想的批判和否定。也就是说,主流批评话语正是通过肯定王朔写作对于解构社会主义时期价值理想的意义,通过肯定王朔式“痞子行状”包含的种种“颠覆性”因素,才将王朔塑造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开路的“痞子英雄”。
王朔这一公众形象的确立,同时也为一种原子化的个人观念——放逐精神理想,丧失对社会、他人的责任感,以自我为中心,释放物质欲望,沉迷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将世俗幸福和个人功利作为唯一的人生目标等——提供合法性,为这种观念的确立开辟了道路。
但是,王朔这一公众形象却遮蔽和剔除了其小说中深刻的心理创伤,说得通俗点,遮蔽和剔除了王朔伤心的一面。因此,要破除主流批评话语对王朔的遮蔽,首先就要解读王朔相关作品,将这一面重新呈现出来,然后再回答这一面与王朔的“痞”究竟是何种关系。

伤心的王朔
陈思和曾在《黑色的颓废》一文中谈到,“王朔笔下的主人公只有一个肉身”,其通常是身兼叙述人和主角的“我”,也可化名为不同的人物,“他们有着十分相似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做着同样的梦,依循着同样的人生原则。”9据此,文章认为早在《空中小姐》中王朔就交代了“这个身份固定的叙事人的真正来历”:他是个退伍军人,1970年代参军,“其军人模式是按照那个时代的理想塑造的”,“可是在他离开军队时,中国社会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商品经济冲击了传统的文化规范”;他发现自己无法适应新的现实世界,只能痛心疾首地注视着自己“怎样一步步堕落下去”,但他同时还企图自救。小说《空中小姐》中叙事人与阿眉的梦中重逢,就是一种“自救”的企图和努力。文章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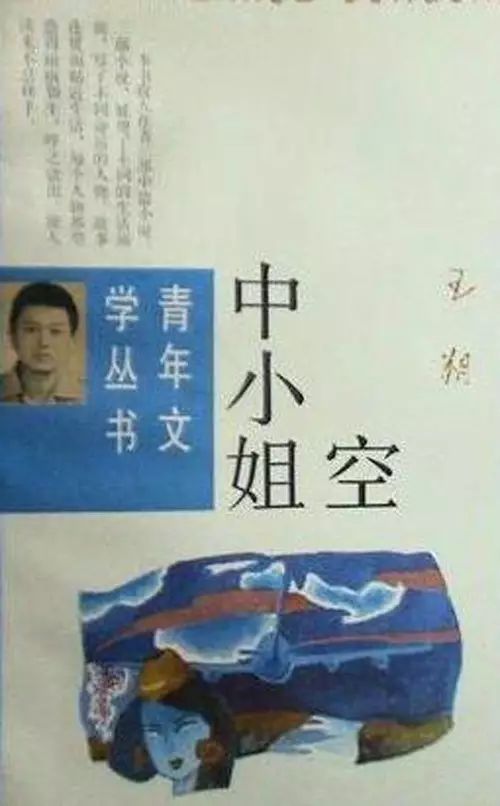
这个梦包含了“王朔式英雄”的性格发展的起点。这个梦象以后随着主人公“我”的堕落一步步淡化,甚至远离他,可是在王朔的小说里它成了一种神秘的力量,时隐时显地浮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启迪着“我”久被封藏的良知。以后,王朔的小说里总是出现一个纯情女孩的意象,千篇一律,她是王眉生命的延续,也是那个梦想投射在尘世的幻影。她在“王朔式英雄”的心目中是绝对神圣的,尽管这位主人公在人生道路上不断滑向商品社会的污浊层面,也尽管这个梦象对他越来越模糊,甚至难以记忆。10
的确,王朔作品中有不少纯情小说,大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叙述人不管是否和王朔共享曾经的1970年代军人身份,与作者之间都没有明显的距离,因此这个叙述人常常是作者的代言人。而在叙述人的经历中,总会出现一个纯情女子形象,这个形象“启迪着‘我’久被封藏的良知”:其或者与“我”有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或者与“我”短暂相逢惺惺相惜,但最终离“我”远去,随之而来的则是“我”深切地追念和不可复得的伤心。
这些讲述男女纯情故事、抒发伤心体验的小说,感动了千千万万青年读者,是“王朔热”形成的重要动力,但是其与“痞子文学”批评话语逻辑的抵牾却往往被忽视。这些小说主要有《空中小姐》《永失我爱》《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过把瘾就死》《动物凶猛》等。下面对这些作品作一些分析。
《空中小姐》讲述“我”与阿眉的感情故事。叙述人与王朔一样曾经具有1970年代军人身份。如小说中所言,“我”原本是“作为最优秀的青年被送入部队的,如今却成了生活的迟到者”,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胖子”。而阿眉如今则是一个令无数人羡慕的空中小姐。“我”和阿眉的处境相差甚远,爱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阿眉崇拜那个过去的“我”,即1970年代那个英姿飒爽的海军战士。这种崇拜可以让阿眉接受“我”现在的一切,但是却不能消除“我”对自身处境的敏感和自尊心受到的伤害。昔日理想的失落、现实的无可适从、与阿眉身份地位的差距,迫使我最终忍痛提出分手。当阿眉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后,“我”得知阿眉对“我”的爱始终如一。
这篇小说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笔触很少进入阿眉的内心世界,因而阿眉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而只是“我”主观心理的投射。所以,阿眉对“我”的爱只是“我”往昔英武形象和军人身份的见证。而1970年代的军人身份记载着社会主义时期的价值理想,因此,阿眉这个纯情少女形象正是这身份记忆和价值理想的隐喻。“我”对阿眉的苦苦追恋,体现的是“我”对1970年代军人身份的认同和对那个年代价值理想的缅怀。小说最后,阿眉来到“我”的梦中,把她全部的情感和力量赠予“我”,让“我”获得新生。实际上,这恰恰彰显出“我”对于她所承载的身份记忆和价值理想的难以割舍之情:
阿眉来了!
冰清玉洁,熠熠生辉。
她拥抱了我,用空前、超人的力量拥抱了我,将我溺入温暖的海洋中。她用岩浆般沸腾的全部热情,挤压着、置换着我体内的沉淀污垢物;用她那晶莹清冽的全副激情,将我身心内外冲刷得清清白白。我在她的拥抱,治疗下心跳、虚弱、昏厥,她的动作温柔了。蓦地,我感到倾注,像九溪山泉那样汩汩地、无孔不入地倾注,从她的心里。流速愈来愈快,温度愈来愈高,我简直被灼疼了。天哪!这是她贮存的全部鲜血、体液,是她积蓄的,用来燃烧青春年华的能量,她再发出耀眼的光亮,就无偿、慷慨、倾其全体地赠予了我。我感到一个人全部情感和力量的潜入,感到自己在复苏,在长大。我像一支火炬熊熊燃烧起来。而阿眉,却像一盏熬尽了油的小灯,渐渐黯淡下去,微弱下去。我清晰地看到她泪流满面却是微笑着,幻作一个天蓝的影像,轻松地、一无所有地飘飘升飞。11

陈思和认为,这个梦虽然体现了叙述人自救的企图,但是“没有什么新意”:“在寓意上它是以一个人的死来更新另一个人的生命,也没有摆脱传统英雄主题的理想色彩;它的内容写死者用鲜血、体液倾注生者的肉身,更未摆脱浪漫主义爱情永恒的含义。”12的确,在当年的“王朔热”中,这篇小说对以往时代价值理想和身份记忆的追恋,往往被批判和否定“乌托邦时代”的人们视为落入了传统的窠臼。《十作家批判》一书“给王朔的所有中短篇小说排名次”时,把这篇小说排在“中等偏下”。13《王朔再批判》一书认为这篇小说不过王朔“痞子文学”的初级阶段。14《王朔批判》一书则认为,这篇小说虽然“完成了一个曲折故事的真实叙述”,但还只是体现了后来小说所写的那种“痞子”、“顽主”的某些因素,不过是王朔“向自己的感觉靠近,唤醒自己潜在话语”的过渡。15
当时主流批评话语讨论这篇小说的重点是关注它在多大程度上“痞”,或者多大程度上不“痞”。这种归类式的思维首先是坚持某一种评价标准,然后用所持标准来衡量这篇小说。在这种封闭的评判方式下,只有排除那些事关社会主义时期价值理想和作者身份认同以及心理创伤的内容,这篇小说才能被赋予意义。由此也可见出“痞子英雄”这一公众形象对于王朔另一面的遮蔽。
《永失我爱》与《空中小姐》有几分相似,讲述“我”与纯情女子石静的生离死别。小说中,“我”是建筑工地的一位卡车司机,由于一次见义勇为、扑火救人的高尚行为,“我”患上了不治之症。为了不拖累未婚妻石静,“我”向她隐瞒了病情并故意制造自己负心的假象,终于迫使她和“我”分手。最后,石静知道了真相,在她的泪眼注视中,“我”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这篇小说中,纯情女子离“我”远去的原因不再是她的牺牲而是“我”的罹难。小说借此深切缅怀以往时代所倡导的高尚无私、纯洁坚贞的爱情关系;与此同时,通过描写工友们对待“我”和石静婚变的态度,呈现了对于工人阶级身份的认同。
小说这样描写闻讯而来的工友对“我”的劝告:
“别喝了!你胡说什么?你哪有什么‘情儿’,我天天和你在一起还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
“我凭什么就不能有‘情儿’?”我翻着白眼拿腔拿调儿地说,“别太瞧不起工人,工人怎么啦,工人勾搭起人来也有手腕着呐。”
“何雷,”董延平双肘压在桌上,充满感情地说,“咱是老粗但不是流氓对不对?见异思迁吃里扒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都是知识分子好干的事儿。咱们,你也不是一向顶瞧不上?”
⋯⋯⋯⋯
“何雷,咱祖祖辈辈可没出过流氓。”16
这番劝告呈现出工人群体对于人际关系的理解:一位工友在爱情婚姻上的背信弃义,并不仅是你自己的事情,不仅有损你的人格,而且损害整个工人队伍的形象和荣誉。所以,董延平劝说“我”的方式不是说“我”的负心怎么对不起石静,而是说这不符合咱们工人阶级的原则——“咱是老粗但不是流氓”。这传达出的无疑是社会主义时期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小说中进一步描写当“我”不听劝告一意孤行时,工地上的同事们表现出来的义愤、轻蔑、鄙夷,就连食堂卖饭的胖姑娘都对“我”满面冰霜,饭菜也给得比往常少得多。而且,工地医务室大夫吴姗为了帮“我”实现不拖累石静的目的而甘愿扮演“第三者”,同样遭到激愤的同事们的一致谴责。这些或许会被某些自由主义者指责为干涉私人生活,妨碍“消极自由”,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专制吧。因此,小说表达的依然是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情感经验、身份认同和价值理想的缅怀以及对其不可复得的感伤。小说结尾这样描写石静来到病房探望“我”的情景:
石静向我移步走来,她晶莹透明,肤若蝉翼,她的眼睛像浸于一缸清水的雨花石,纯净滑润⋯⋯
我面无表情地望着她——我已经无法作出任何表示了,连笑一下也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种东西还是自由的,它从我眼中流出,淌过我毫无知觉的面颊,点点滴在那只向我伸来的美丽的手⋯⋯17
石静“那只向我伸来的美丽的手”象征的是纯洁无私、高尚坚贞的爱情关系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但如今面对其召唤,“我”已无法作出回应,“我”正在离它远去。这当是小说题目“永失我爱”的深刻寓意。而这种寓意与“王朔热”中真/假命题存在明显的抵牾:在真/假命题中,“痞子行状”被说成是符合真实人性的,而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则是虚假的,被认为是王朔所要消解和颠覆的东西。主流批评话语与小说文本之间的这种抵牾,彰显出王朔公众形象建构过程中对异质性情感和精神资源的排斥与剔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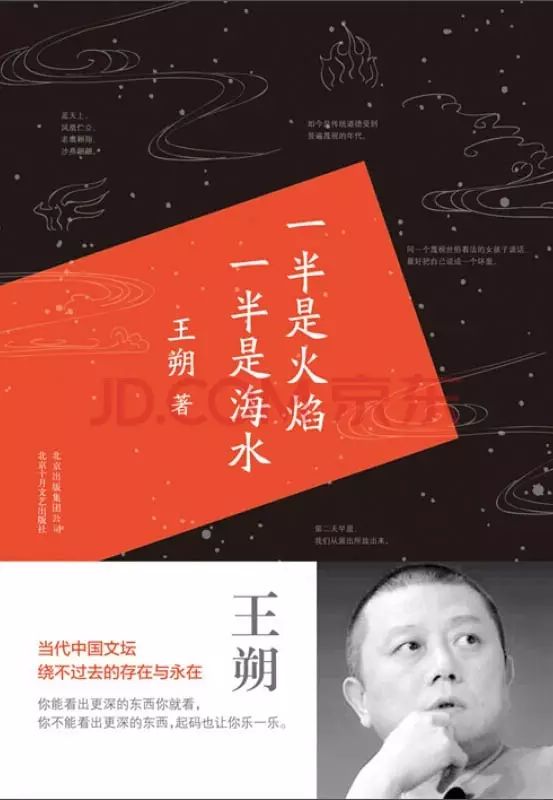
与以上两部作品相比,《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更多地展示了王朔式的“痞子行状”,根据其改编的电影当是“痞子论”的重要依据,但是同样被当时论者划定为“准痞子文学”,这或许是因为其一方面展示了“痞子”的生存状况,另一方面表达了对这种状况的痛切反思。这部小说分为上下两篇,分别塑造了两个纯情女子形象:吴迪和胡亦。这两个形象之间有密切关联,共同构成改革初期某种精神症状的隐喻。
小说中,叙述人“我”原本是一个组织卖淫再冒充警察敲诈勒索的“痞子”。由于对纯洁的女大学生吴迪的勾引和抛弃造成她的沉沦和自杀,“我”极度伤心愧疚。这使“我”出狱后又充当了保护、救助纯情女子胡亦,惩治流氓的英雄角色。其中,令人深思的是,“我”在勾引吴迪的过程中,对自己恶劣品行的介绍,句句都是实情,但是在吴迪看来,却是一种好玩和有趣。这是“传统道德受到普遍蔑视的时代”给吴迪造成的深刻影响,“我”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才达到了勾引她的目的,而这也最终导致了吴迪发现真相后的悲惨结局。
胡亦是吴迪这一形象的延续,她也是有反叛意识的女大学生,由于鄙视传统社会规范和中国式的“假深沉”,故意作出放荡形骸的样子,后被两个自称作家的流氓诱奸,只是在“我”的救助下才没有走向沉沦和堕落。在胡亦与那两个流氓的接触过程中,“我”一直告诫她不要上当受骗,但“我”的话都被她视为“乏味”、“假深沉”。她用与“我”当初对吴迪说过的一模一样的话来嘲笑“我”。这当然是作者的有意设置,意在形成强烈的讽刺效果。而且在“我”与胡亦的交往中,也设置了多处与“我”和吴迪交往时相同的场景和对话。正是通过这样的设置,作品表达了对“痞子行状”和改革初期社会精神症状的质疑和反思。
《橡皮人》延续了上述社会反思的逻辑。小说以叙述人“我”和一帮同伙在某经济特区非法倒卖汽车电器为线索,表现这个群体生活的堕落和人际关系的丑恶。但是,这里仍然出现了一位纯情女子的形象,她叫张璐,是女兵,革命军人的女儿。虽然“我”们一帮男女同伙之间性关系非常混乱,但张璐是“我”决不忍心染指的,她的纯洁使“我”不会产生任何非分之想,就连同伙张燕生都严肃地告诫“我”:“别碰她。”张璐使“我”和张燕生想起了美好的童年往事,也使“我”当晚做了一个恶梦:“我”处在“万木凋零”、“虎狼相伴”的荒原,近在咫尺有一“锦绣之地”,但随之地裂,锦绣之地渐渐远去,可望而不可即,“我在荒原哭泣”,随后变成了啮食生肉的非人。小说中,这种强烈的异化与非人化的感觉经常伴随着“我”。最后“我”变成了橡皮人,同时又见到已经结婚的张璐。可见,张璐这一纯情少女形象寄托了“我”的某种渐渐远去但又难以割舍的理想和记忆,这使得“我”对当前龌龊的生活状态产生强烈的质疑和痛切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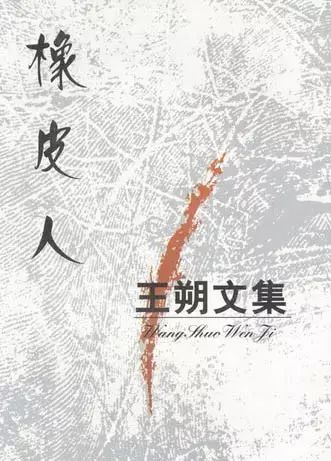
如果说《空中小姐》和《橡皮人》分别代表了“追念过去”和“反思现状”这两种叙事逻辑,那么,在《过把瘾就死》中这两种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就交汇到了一起。这篇小说讲述了“我”(方言)与纯情女子杜梅从恋爱结婚到婚姻破裂的情感经历。对于这场婚姻的破裂,有两个事件特别关键。第一个是:一天晚饭后杜梅与方言发生争吵,杜梅说了一番挖苦方言的气话,深深刺痛了方言。在争吵暂时平息后,小说中这样描写方言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创伤:
实际上我最激烈的思想活动没有告诉杜梅。那种令我齿冷令我感到受到严重伤害的感觉一直带到我们上床睡觉,甚至连做爱也没有使我忘掉它。尽管我知道她是无心的,但我也不能原谅她。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原谅过任何人。我可以容忍别人对我的谩骂、攻讦,容忍别人怀疑我的品质,哪怕贬低我的人格,但我决不容忍别人对我能力的怀疑!此辈我定要追至天涯海角,竟我一生予以报复。我活着、所作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些曾经小觑过我的人逐一踩在脚下!18
这样的心理创伤显然超出了家庭争吵的范围。实际上,不是杜梅的挖苦给方言造成这种心理创伤,而是杜梅的挖苦击中了这种心理创伤。这心理创伤构成了方言与杜梅矛盾激化的潜在心理依据。第二个事件由肖超英、潘佑军在方言家喝酒引起。他们三人本是一起长大的哥们,一起参军的战友,方言和潘佑军复员回到北京,而肖超英留在部队当了干部,他回京探亲,三人聚在方言家喝酒。三人深情地追忆昔日的部队生活及在全军比武中各自的英勇表现,酒从中午喝到下午、喝到天黑。杜梅下班回家后,实在忍无可忍,终于下了逐客令,这让方言对她大打出手。小说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
这时,我脑袋忽地一热,像什么成块成吨的东西忽然迸碎了,衬衣的扣子也绷掉了,站起转身抡圆了就是一个大耳光结结实实贴在杜梅的脸蛋上。随即破口大骂:
“你也太不懂事了!轰他妈我们哥们儿。我们多少年没见了?告诉你要滚你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没你呢!”19
正是这次轩然大波将方言和杜梅的感情推向了冰点。
这两件事有着内在联系。先就第二件事来说,方言之所以瞬间失控大打出手,是因为杜梅的逐客令冒犯和嘲弄了方言的身份认同和记忆。上引杜梅下逐客令后“我”脑袋里忽然迸碎的“成块成吨的东西”,正是方言他们三人深情追忆的1970年代的军人身份,这种记忆是方言深埋心底、非常珍视的。如果仅仅把他的粗暴归因为在哥们面前尽失颜面,就很难解释后面方言一直未对自己的粗暴感到愧疚,也从未向杜梅道歉的表现。这种似乎不合常理的情节安排暴露了作者的无意识:方言的行为是正当的,方言珍视的东西不容冒犯!这彰显出作者对方言行为的高度认同,方言和作者共享着同样的军人身份记忆和自我意识。
明了上述心理逻辑后,就不难理解第一件事中方言(作者)的心理创伤。方言珍视的军人身份记载着昔日的英雄本色和价值理想,但因时代转变,这些变得一文不值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言们(作者)是时代转变的弃儿。正是这种强烈的被遗弃感造成的心理创伤,使他对自己如今的处境特别敏感,一旦遭到小觑,就激起他强烈的甚至恶毒的报复心理,哪怕是对于杜梅。而他之所以可以容忍别人对他的谩骂、攻讦,对他品质的怀疑、人格的贬低,是因为他不接受当今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是因为他的叛逆。而这种叛逆心理和报复心理具有同构性,都是时代转变造成的心理创伤的反应。

如果说上述内容是《空中小姐》代表的叙事逻辑和心理逻辑的延伸,那么通过方言和杜梅的婚姻关系,这篇小说同时还补全了《橡皮人》中叙述人“被遗弃荒原”的荒诞处境背后的心理逻辑。小说开头说:“杜梅就像一件兵器,一柄关羽关老爷手中的那种极为华丽锋利无比的大刀。”20杜梅性格的锋利体现在她对爱情的偏执乃至疯狂的追求上。她的柔情蜜意背后是敏感多疑、刚强固执、歇斯底里。这种杜梅式的爱情有幼时家庭变故的影响——其父因婚外恋杀死其母,但更是时代转变的产物。随着时代转变,理想主义在社会领域退场,以往时代的理想和激情转移到了个人爱情领域,铸就了杜梅式的爱情——理想主义的爱情。而对于方言来说,他的问题是并未实现这样的转移,他无法在柔情蜜意的家庭生活中安顿身心。他在与杜梅的激烈争吵中道出了心里话:“我那么在乎每天下班回来能捏着小酒盅啃猪蹄子你坐在旁边含情脉脉地望着我?我那么在乎冬穿皮衣夏穿纱那么在乎被窝里有个热身子?”21这表达出方言自我意识中对庸常生活的蔑视,这同样是时代转变造成的心理创伤的反应。对家庭生活的不同态度导致婚姻破裂。婚姻破裂对于方言来说是生活更加无聊,是对生活更加没有感觉,而对于把理想和激情都押在爱情上的杜梅来说,则意味着灭顶之灾。
小说结尾,一个午夜,方言、潘佑军等人在偏僻的马路上遇见杜梅一个人骑车狂奔,当方言等人拦住她的时候,只见她“头发披散、眼露凶光,像个巨大凶猛的猩猩”22。当方言等人抬她上车时,她的拼力挣扎、对众人的攻击、令人“毛骨悚然”的哀号证明她精神的疯狂状态,而且醒来竟不自知。正是这一夜方言发现自己是“那么爱她”。小说中这样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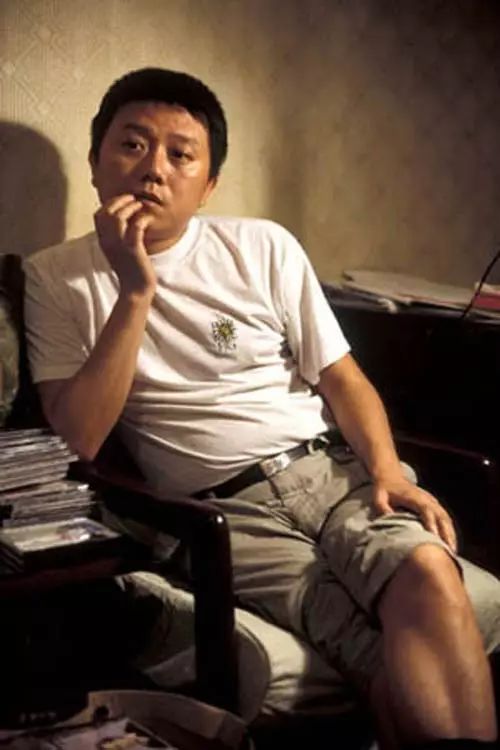
那天夜里,我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那种巨大的、澎湃的、无可比拟的、难以形容的、过去我从来不会相信会发生在人类之间的激情。
这情感的力量击垮了我,摧毁了我,使我彻底崩溃了。我不要柔情、不要暖意,我只要一种锋利的、飞快的、重的东西把我切碎,剁成肉酱,让我痛入骨髓!23
当时崔健的摇滚歌曲里有一句流行歌词:“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对崔健赞赏有加的王朔在这里表达了同样的感受。这种感受是时代转变造成的精神症状。杜梅由全部生命激情铸就的爱情之刀,让“我”猛然有了存在的感觉,“我”愿被剁成肉酱痛入骨髓,因为这可以让我不再是没有感觉的“橡皮人”。以上当是“过把瘾就死”这个小说名字的由来,也是《橡皮人》中未被言明的心理逻辑。
通过对王朔纯情小说进行文本细读,我们呈现出了“伤心的王朔”的基本面目。概括地说即:第一,对社会主义时期价值理想和身份记忆的难以割舍和不可复得的伤心;第二,对“痞子”的生存状态和改革初期社会精神症状的痛切反思。在此基础上,就可进一步讨论:王朔的“痞”到底从何而来?对于这个问题,上述心理逻辑已经提供了解答的线索,而《动物凶猛》则正面作出了回答。

《动物凶猛》的秘密:王朔的“痞”从何而来
《动物凶猛》发表于1991年,是王朔创作鼎盛期的总结性作品,是王朔写得最为深情的一篇,也最被他自己看重。小说开头这样写道:
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自我慰藉。
我很小便离开了出生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作故乡。这个城市一切都是在迅速变化着——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它已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崭新、按我们的标准挺时髦的城市。
没有遗迹,一切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24
以上文字,首先把乡村(故乡)与城市(故乡)这种空间的差别转化成时间的差距。因乡村(故乡)变化缓慢,所以可充当以往时代经验和记忆的载体,而城市(故乡)却没有这样的可能。作者自小生活的这个大城市已完全改观,以往时代“没有遗迹,一切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自然,“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也就无从寄托。那么,“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是什么呢?接下来作者写道:
我在人前塑造了一个清楚的形象,这形象连我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不论人们喜爱还是憎恶都正中我的下怀。如果说开初还多少是个自然的形象,那么在最终确立它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多种复杂心态的左右。我可以无视憎恶者的发作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了醋。
我想我应该老实一点。25

这里作者对自己的公众形象直接进行审视。从个人名利的角度讲,这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公众形象“连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但是,自己知道它并不是自然的,在确立它的过程中,自己“受到了多种复杂心态的左右”。“多种复杂心态”当中自然包含着迎合主流话语建立自己社会名望的动机。而“为了不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作者坦陈这个公众形象违背自己的初衷和本意,它就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了醋”。所以,作者这一次要“老实”地讲一些隐藏在内心当中真实的东西。
接下来,作者深情地讲述了“我”青少年时代和米兰之间的感情故事。故事发生在1970年代中期的北京,很多人认为那是个“专制”的时代,但这个故事却给孩子们打开了一片“自由的天地”:“我”们不必再遭受父母和老师的监管,可以自由自在,无所顾忌。这为“我”和米兰的结识提供了机会。“我”在一次溜门撬锁的游戏中,潜入米兰的闺房,发现了她的照片;后来和一群雄踞街头的少男少女被解往派出所时见到了米兰。小说这样描写两次相见的感受:“那个黄昏,我已然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正常反应,视野有多大,她的形象便有多大;想象力有多丰富,她的神情就有多少种暗示。”26“但我看她的第二眼,这个活生生的、或者不妨说是热腾腾的艳丽形象便彻底笼罩了我,犹如阳光使万物呈现色彩。”27
“我”自见到米兰的照片就深深地迷恋上她,日复一日地守候在她家楼房前,热切期待着她的出现,甚至为自己被她牢牢抓住无法解脱而感到恐惧。而且,和米兰结识后,会因渴望见到她而失去正常的感知,出现种种难堪症状。但只要一见到米兰,那些症状就都消失了。“我”对米兰的迷恋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当和米兰单独相处时,“我”又老实又听话,没有任何“痞子”相,即使有时故意吹嘘自己干过的荒唐事,也是为博得她的青睐。“我”甚至显得可怜巴巴,不敢说话,不敢正眼看她。在她面前,“我”自甘于一种弱小的从属地位,渴望获得她的关爱。
和米兰一直保持这样的关系,自然是“我”梦寐以求的心愿,但情况发生了逆转。当“我”为了炫耀而把米兰介绍给高晋他们之后,“我”逐渐发现米兰和高晋的关系越来越不一般,米兰正逐渐离“我”远去。这时,一种痛苦的被遗弃感改变了“我”对她原来的美好印象:
我对米兰说话的措辞愈来愈尖刻⋯⋯她在我眼里再也没有当初那种光彩照人的丰姿⋯⋯一言以蔽之:纯粹一副贱相!
我再也不能容忍这个丑陋、下流的女人⋯⋯28
这里对米兰的贬斥与前面的礼赞形成鲜明反差。痛苦的被遗弃感使得“我”一下子变得“痞”态百出,挖空心思想出种种“痞”方对待她。“我”对米兰的这种惊人变化,实际上正是因为“我”对她的深切眷恋和难以割舍。“我”的“痞”是遭她遗弃之后极度伤心的非正常反应。当“我”最终意识到自己被彻底遗弃时,“我”强暴和亵渎了米兰——而这,恰恰意味着永远的失去了她。小说结尾写道:“我抽抽嗒嗒地哭了,边游边绝望地无声饮泣。”
小说为我们编织了这样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但有意味的是,小说一边讲述这个故事,一边又解构这个故事:
我发现我又在虚构了。开篇时我曾发誓要老实地述说这个故事,还其真相。
可我还是步入了编织和合理推导的惯性运行。
背叛我的就是我的记忆。
我和米兰从来就没熟过!29
小说中这种解构故事的文字反复出现,不断打断故事进程,但作者又按照原有逻辑把故事强行讲完。如果不把这仅看作是卖弄“现代派”的叙事技巧,而是另有深意,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其实是暗示读者:“我”和米兰的故事并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米兰这个纯情女子是作者珍视的以往时期价值理想的隐喻。小说中还有一位放荡的女子于北蓓,她总是在米兰不在场的时候出现,在她和米兰身上,作者寄托了不同的感情和想象。于北蓓代表着身体欲望的一面,她是使“我”堕入欲望陷阱的诱因,而“我”对米兰的迷恋则没有什么身体欲望搀杂其中:“那时,我真的把自己想成是她的弟弟,和她同居一室,我向往那种纯洁、亲密无间的天然关系,我幻想种种嬉戏、撒娇和彼此依恋、关怀的场面。”30因此,米兰承载着作者青少年时代纯真的理想和珍视的价值,这正是小说开头所说的“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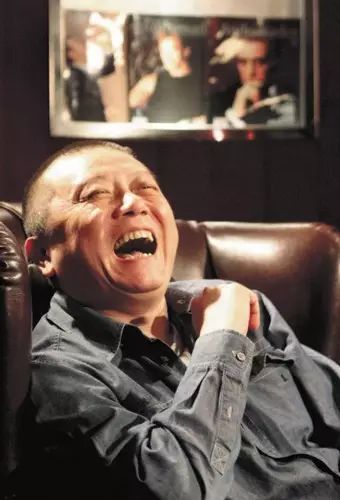
这样,王朔深情讲述的这个“我”和米兰的感情故事就揭示出王朔的“痞”究竟从何而来:因为时代的转变,社会主义时期的价值理想猝然远去,遗弃了王朔,所以他才示以种种“痞”相。也就是说,王朔的“痞子文学”对社会主义时期价值理想的种种嘲讽和诋毁,正是因为时代转变自己被这价值理想遗弃后极度伤心的非正常反应。这反证了王朔对以往价值理想的难以割舍。因此,当亵渎了这价值理想之后,他就像亵渎了米兰的“我”一样陷入无限的空虚、麻木与绝望之中,陷入方言们共享的“橡皮人”一样的荒诞处境之中。这正是《动物凶猛》要揭示的秘密,也是王朔要老老实实讲这个故事的真意所在。
在《我是王朔》一书中,王朔曾深情地说道:
我认识到理想主义的问题。但咱们这一代人,说实话,哪能没有理想啊?我对真正的理想是珍视的,我不允许别人利用这些东西来诱惑我。⋯⋯人类有时需要激情,为某种东西献身是很大的东西,我并不缺少这种东西。但这种东西必须出自内心。我看到的却是这些美好的东西被种种的学说被资产阶级自由化,被亡我之心不死的别有用心的人给毁地差不多了。
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割舍的。《动物凶猛》就流露出我对那种已经彻底消失的东西的一种缅怀,有非常强烈的怀旧情绪。

我第一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他写出了我们与环境之间难于割舍的,血肉相联的关系,可是现在又有了矛盾。⋯⋯那种环境毕竟给了你很多东西。所以看苏联这种情况,我特矛盾。我们青年时代的理想和激情都和那种环境息息相关,它一直伴随着你的生命。
说我的作品痞,这是总的错了。其实我的作品不痞。虽然其中有油滑调。31
这些内心表白,袒露了王朔对社会主义时期理想和激情的珍视与缅怀。王朔同时还说明了理想和激情发自内心与以之蛊惑别人的区别。这或许正是《动物凶猛》中“我”经由自己的探索而迷恋上米兰的原因——米兰代表的价值理想正是出自他自己的内心。王朔的以上表白和言说是在1992年5月,非常接近作品创作的时间,与作品中所抒写的思想内容正可相互印证。
这显然可以见出,王朔并非如当时主流批评话语所说的:是因为看透了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欺骗性和伪善本质,才用种种痞的方式嘲讽它,诋毁它。正好相反,王朔的叛逆、他的“痞子文学”恰恰源自他对往昔时代价值理想不可复得的伤心。也就是说,王朔“痞”的一面和伤心的一面具有同构关系,是那个年代王朔们同一心理结构的两个方面。
这也显然见出,当年主流批评话语在建构王朔公众形象的过程中,如何对王朔小说提供的经验进行选择、剔除和删改,如何操控着王朔文本意义的生产,如何将社会主义时期的价值理想和经验记忆毫无反思不由分说地清除出去,从而构造出一套关于个人、自由、解放、欲望的神话,向全球资本主义顶礼膜拜的神话。
1 “王朔热”前后有三次,第一次是由1988年王朔的电影热引发的关注;第二次是90年代初,由王朔参加编创的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陆续上映产生轰动效应,再加之他个人文集的出版,引发社会对他创作(包括影视创作)的全面关注,这期间王朔还成立了“海马影视创作中心”、“时事文化咨询公司”,更加助长了其声势;第三次由1999年末王朔挑战金庸引起,广大“金庸迷”群情激愤,各媒体也追踪报道,其中网络得风气之先,形势很快发展为“王朔批金庸,大家批王朔”,金庸的支持者和王朔的支持者之间展开激烈论战,但王朔一边明显占劣势。这一讨论并没持续多久,也没产生多大影响,可看作“王朔热”余绪。本文中“王朔热”主要指前两次。
2 黄平:《没有笑声的文学史——以王朔为中心》,《文艺争鸣》,2014年第4期。
3 王朔:《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天涯》,2000年第2期。
4 邵牧君:《王朔电影热缘何而起?》,《中国电影报》,1989年3月25日
5 萧元:《王朔再批判》,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70-71页。
6 赵园:《“难见真的人!”——试说〈轮回〉改编原作的得失》,《电影艺术》,1989年第5期。
7 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8 金笛:《何必“谈朔色变”》,《中国青年报》,1993年2月13日。
9 陈思和:《黑色的颓废——读王朔小说的札记》,《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5期。
10 同上。
11 《王朔文集》(1),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85-86页。
12 陈思和:《黑色的颓废——读王朔小说的札记》。
13 朱大可等:《十作家批判》,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6页。
14 萧元:《王朔再批判》,第71页。
15 张德祥、金惠敏:《王朔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5-46页。
16 《王朔文集》(3),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233页。
17 同上,第239页。
18 王朔:《王朔文集》(4),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386页。
19 同上,第395页。
20 同上,第333页。
21 同上,第420页。
22 同上,第437页。
23 同上,第439页。
24 同上,第248页。
25 同上,第248—249页。
26 同上,第255页。
27 同上,第273页。
28 同上,第316、317页。
29 同上,第321、322页。
30 同上,第289页。
31 王朔等:《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第80、34、76、27页。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