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去真正的西双版纳,吃一顿雨林杀猪宴
原创 你们的 ELLEMEN睿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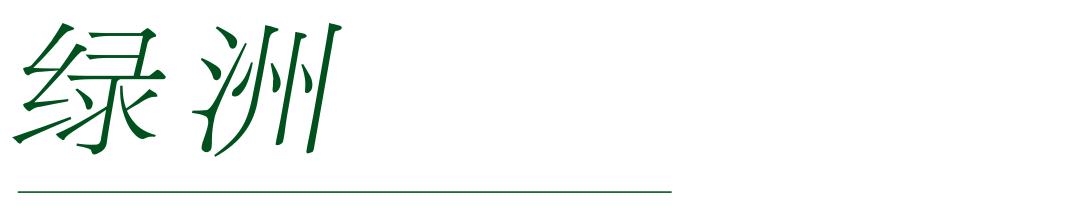
去年7月末,我们一行人抵达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相较国内其他地区过度开发的现状,目前,西双版纳依旧保存了大片原生态的热带雨林及热带季雨林,这也是北回归线沙漠带上仅有的一块绿洲。
想要探索这块绿洲,在雨季到来之前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西双版纳一年只分旱雨两季,每年的5月至10月为雨季,多暴雨,降水量占全年总降水的80%以上,但这却是丛林最繁茂的时刻,丰沛的雨水催发了茁壮的生机,叫醒漫山的野生菌,也营造出云雾缭绕的自然奇观。
位于勐仑镇大卡村的大卡新寨,是我们抵达西双版纳后的第二站。驱车从景洪市区出发,要花去一个多小时,经历昆磨高速和一小段狭窄的盘山路,才能最终抵达这座被山林怀抱的村寨。
寨子里生活着99户人家,都是爱尼人。作为“自然之子”哈尼族的分支之一,爱尼人集中分布在西双版纳州南部和普洱市的澜沧县,以及缅甸、泰国、老挝和越南的山区。与聚居于红河地区,因梯田开筑技术闻名的哈尼族人不同,世代生活在高山之上的爱尼人更依赖原始森林,曾长期保持着“游耕”的生活方式,他们内部讲究一切平均分配,自称为“阿卡人”。

西双版纳州分为“一市两县”,即县级市景洪、勐腊县和勐海县。景洪拥有最常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的星光夜市、大金塔寺等热门的游客“打卡地”,还有成列的高楼大厦和整洁的城市街道。不过,同行的本地摄影师告诉我们,“来到景洪不算到了西双版纳”,人为雕琢的城市景观之外,才藏着真正的西双版纳。
经营口岸贸易和餐饮生意的阿卡商人夫妇安伞和书溢,是我们本次雨林探索行程的主要策划人,在两人和十余个村民的带领下,我们搭乘皮卡车从寨子里出发,穿过几幢低矮的砖房,迎面“撞”上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水稻田。安伞告诉我们,稻谷是阿卡人的重要主食来源,其中又分水稻(梯田种植)和旱稻(梯地种植),相较如今更为常见的水田,受限于当时的自然环境和农耕水平,他们的祖辈更依赖“水、土和肥料都是靠天”的山谷梯地。
“种山谷先要砍掉山上的树木,把地烧了,这样杂草和土壤里的一些害虫也会被烧掉。留下来的草木灰慢慢发酵,就变成了天然的肥料。”书溢补充道。她和丈夫安伞都是“80后”,他们的童年时代,从原始雨林迁徙至大卡村才几十年的族人们还在大量种植山谷,但上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作物橡胶成为大卡村的重要收入来源,传统的山谷地就逐渐被橡胶种植林取代。
在安伞看来,阿卡人种植山谷,“是在挑战自然,也是在遵循自然规律”。他们采用“抛荒”的方式来减弱“刀耕火种”对原始森林造成的破坏——比如,在新开荒的“处女地”上耕作一年后,就去寻找下一片林地,让旧谷地休养生息。因为之前有意识地留存了原来的树桩,“不挖不犁”的开垦方式也保护了树木的根系,退耕的土地很快能重新长出森林植被。

大卡新寨位于勐腊县勐仑镇境内,距离寨子四公里处就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其保存有一片面积约250公顷的原始热带雨林,是我国面积最大、收集物种最丰富、专类园区最多的植物园,也是世界上户外保存植物种数和向公众展示的植物类群数最多的植物园。
千禧年后,随着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响应国家“保护雨林、保护生态”的政策号召,大卡村的村民不再过度依赖传统的山谷种植。不过,生活在老挝、缅甸等地的阿卡人,部分依旧聚居在高山之上,还保持着“刀耕火种”的农作方式。
车辆继续往前,紧邻水稻田的是沿山势铺展开来的成片橡胶林。在热带植被与橡胶树交错的泥泞山路上剧烈颠簸20分钟后,我们抵达一处斜坡,安伞告诉我们,这里就是森林的入口。顺着眼前这段接近60度倾角的野径往下有一处溪水,溯流而上,我们就能进入雨林,见到这个世世代代哺育阿卡人的自然“母亲”。

我们进入雨林这天是一个暴雨过后的透亮晴日,随行的当地摄影师提醒大家注意防晒,因为这里的阳光毒辣,直射在人裸露的皮肤上,只需片刻就有刺痛感。不过,随着队伍逐渐深入丛林,明晃晃的太阳便不再是我们的困扰,高耸的浓密树冠将阳光切割成细碎的光斑,只偶尔掉落在潮湿的地面上。

阿卡人会在山谷地旁种上一些瓜果。平日里,这些瓜果的藤蔓、茎叶是可供食用的蔬菜,而待到山谷成熟,瓜果们也次第挂果成熟,大家就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林间静谧,只余淙淙溪水、幽幽虫鸣,伴随着间歇响起的鸟雀叫声。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绿色景观和变成四个沉默的灰点的手机信号,无不在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少有人类踏足的自然世界。
阿卡人郎海是我们的向导,也是大卡新寨周围环绕的1349亩国有林的护林员。山间植被茂密,没有现成道路,他便领着我们踏着溪边山石而上,去探寻雨林留给人类的馈赠。
虽然不再大量砍伐树木、烧地种植山谷,但热带雨林依旧是阿卡人重要的食物来源。小满之后,降水增多,山林里的各类野生菌,还有水芹菜、水薄荷、酸荞菜、野蕨菜、野苦子……就争先恐后冒出头来。我们跟随郎海向上攀爬了二十余分钟,已经陆续采集到几捧赤红的砂仁果、两株茎叶有半人高的野姜、一种叫不出名字的香料,还有一捆蒌叶和酸荞菜。

阿媲(哈尼语,意为奶奶)晓理正在摘芭蕉花,它的皮呈紫红色,外观看上去像一颗紧闭的莲花苞,切开后,内芯却像是一叠乳白色的细密宣纸。
野芭蕉是我们此行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它在阿卡人的餐桌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芭蕉心(芭蕉树茎中最嫩的部分)和芭蕉花都能吃,芭蕉心可以炒,很好吃,煮了汤也好吃。”郎海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向我们解说如何将野芭蕉制作成美食,并利落地抽出长刀将一株约有两人高的芭蕉树拦腰砍断。同行的妇女迷索摘下枝头饱满的芭蕉花放进背篓,又择出几片宽大的芭蕉叶扛上肩头——阿卡人善用“包烧”的方式来制作美食,这是一种较为古老的烹饪方法,既能保留食材的水分和营养,还能为其增加包裹物的清香,而雨林中最为常见、尺寸各异的芭蕉叶就是“包烧”最适合的包裹物。
野芭蕉有着极强的再生能力,刚被砍断的截面不过几十分钟就往上窜出了一小段儿。对这片森林格外熟悉的郎海告诉我们,约莫一周后,这株芭蕉树就能长回原来一样的高度。

芭蕉叶包饭是阿卡人进山劳作时常携带的口粮,加入森林中能即时获取的新鲜食材,就变成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随处可取又水分丰富的芭蕉心,是雨林中的长途迁徙者的优质补给品。在民间流传的故事里,哈尼族的先民古羌族人自青藏高原一路南迁,行走至云南哀牢山地区时,还不了解雨林中生物的习性,落后的人看到被前人砍过取食的野芭蕉已经长得很高,误以为他们早已走远自己追赶不及,便就地安顿下来。虽然这种说法并无严肃的学术考证,但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哈尼族各分支和与其习性相近的基诺族会由北至南,在被雨林覆盖的群山间分散形成聚落。
不过,除开野芭蕉这类能快速再生的植物,阿卡人并不会轻易砍伐森林中的大树。“我们先要把植物保护好,才能动用森林。”郎海反复强调这一点。
从砍下野芭蕉的地方再顺水往上,就将进入这片雨林的腹地。抬眼看去,四周的参天巨树越来越多,书溢告诉我们,六十多年前,自己的族人们还住在这片雨林深处的高山之上,里面没有路,也没有交通工具,下山至此约有一天多的脚程,“从那上面看下来,这里都是被云层盖住的”。

哈尼族制作美食以烤、煮为主要烹饪方式,其中,包烧的精髓来自外覆的芭蕉叶、各类野菜及佐料。
前路荒芜难行,郎海和迷索便领着我们原途折返。时至正午,安伞的父亲梭安领着几个村民在丛林入口处用砍下的竹子搭建桌椅,还带来了“嚎楚”(哈尼语音译,指芭蕉叶包饭);留在水源下游的妇女飘蹉熟练地在岩缝间摸鱼抓蟹;迷索的姐妹迷霞准备好了酸肉、油渣和香料,只等新鲜的芭蕉心和野菜来制作包烧。
安伞和妻子一起策划了这场“野宴”,“这些野菜包烧,还有那些螃蟹小鱼和芒果拌饭,全都是我们小时候常吃到的”。在他十岁之前,寨子里物资匮乏,对外交通也不便利,族人的生存全都依赖于身后的这片雨林。
“西双版纳物产丰富,雨林里面的阿卡人,只要勤快一点是饿不死的,不过是吃得好,或吃得坏一点。”善于烹饪的书溢整理着新采的野菜,将当地的一句俗语转述给我们:“靠山吃山,才有金山银山。”

穿着传统服饰的梭安带着他的小儿子安珑。哈尼族的服饰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活动场所、身份地位上都有不同的款式区分,是识别着装人的年龄与其社会地位的显著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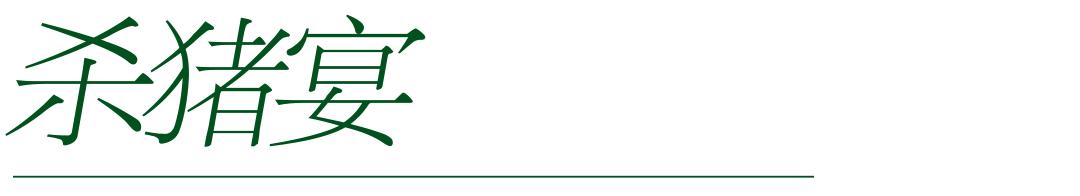
借这次“野宴”,安伞和书溢想要还原阿卡人在热带雨林间劳作的生活图景——在播种和收割的农忙期,阿卡人会带上简单的行囊,连续几天住在森林中的山谷地旁。砍来的竹子、树枝和捡来的草叶能搭出居住的窝棚、制成常用的餐具,随处可见的野菜蔬果、鱼虾鸟雀又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食材。
这也是安伞最难忘的童年记忆。对年幼的孩子来说,雨林虽然充满新奇的诱惑,但也危机重重,只有农忙时节,他们才能跟随家人一同进山待上几天,抓虫子、掏鸟窝,而不是守在寨子里,听着日落时归巢家禽的吠叫,焦急地等待结束一日劳作后晚归的父母。
山谷收割完毕后,从森林回到村寨的阿卡人将会迎来一个重要的节日“新米节”,用以庆祝丰收和感谢土地之神。虽然我们不是在丰收月到来,但大卡新寨的村民们还是特意安排了一场传统的杀猪宴,带我们体验“新米节”的氛围。
“以前生活不好,一年到头一家人就杀一头猪,整年的脂肪摄入也就靠这一头猪。”安伞告诉我们,虽然储藏条件有限,但阿卡人也会想办法将一头猪从年头吃到年尾。在留下宴席当天要吃的新鲜猪肉后,妇女们会将余下的猪肉腌制发酵变成酸肉,或是用柴火熏烤成干巴、晾晒风干制成腊肉,都能有效延长它们的储藏期;至于内脏和猪皮,就炼出猪油,连同油渣一起封进土罐,待日后烹饪时取用。
当然,作为一场宴席最重要的环节,杀猪也有着各种讲究。安伞和书溢邀请寨子里的老人沙格来下刀。“每头猪杀出来的血是不一样的。”安伞解释道,刀尖插进去的部位不同,流出来的猪血的状态也不同,只有经验丰富的老人才能准确判断各种差异,并据此调整清水与猪血的配比,制作特色菜血旺,“我们寨子里,能把猪血弄成果冻状的人应该不超过五六个”。

沙格正在制作血旺,这是杀猪宴上必备的“硬菜”,用不断搅动后的生血掺进熟猪肉及内脏,再加入各式特色作料搅拌均匀,最后凝固成的“果冻”状的待客佳肴。
将生血和鲜肉简单处理后,梭安特意摘来了一块还爬着野蜂子的“小挂蜜”(野生蜂巢),招呼我们尝鲜,转头又和四五位老人在屋外削起了宴席上要使用的竹碗、竹杯和竹筷。手艺灵巧的阿卡人仅凭一把短刀,就能将竹筒做成各式餐具,不过因为制作耗时费力,这类餐具如今多只用于接待贵客,更能彰显主人的用心。
迎接我们的这场宴席声势浩大,除了杀猪时忙前忙后的男人们,妇女们也拿起背篓去田埂旁采摘新鲜的玉米、瓜果。书溢偷偷告诉我们,因为雨季的西双版纳天气变幻莫测,我们的进山计划不能提前确定,一切只能临时安排,乡亲们也是自发赶来,“纯帮忙,他们不图任何,就是想参与在这里”。
身处这样的环境中,你很容易感受到乡民之间的和谐互助,那是一种几乎在现代都市中绝迹的、热情又柔软的氛围。它的形成或许也与阿卡人的传统生活方式相关,热带雨林里物产丰富,却又危机四伏,要想在森林里讨生活,一个村寨的人往往需要联合行动。书溢的母亲六岁时随着族人下迁至大卡村,那时,“整个寨子里的男丁,一般十五岁以上,都要带着狗一起去打猎”。妇女听到丛林里传回的吹牛角声,就知道男人们今天有收获,便在家中生火烧水,等待着处理猎物。
阿卡人对打回的猎物讲究平均分配。“任何东西都分得很均匀,比如说有50户人家,一块野猪心也要切成50份,每家都有一片。”书溢说。哪怕如今不再需要去森林里猎杀猛兽,寨子里还保留着旧习俗,逢年过节,大家如果凑钱一起买一头牛,宰杀后,也会严格遵守平均原则来分配。
随着西双版纳地区整体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近年来不断深化的新农村建设,曾与世隔绝的大卡寨逐渐融进日新月异的主流社会。干栏木楼变成了舒适的砖房,寨子里铺上了水泥路,通了电和自来水,又有了5G网络,年轻一代中像安伞和书溢这样外出谋生的人也越来越多。
阿卡人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正不断发生变化,但在这个被山林绿树包裹着的村庄里,有些东西又似乎从没改变过。午后,往这里赶来的村民越来越多。忙于搬运食材的大哥放下背上趴着的孩子,嘱咐几句,摩托车轮方向一转很快又消失在小路拐弯处,只余表情懵懂的男孩抱着背兜愣在原地。“你看,他们还是很原始很淳朴。”书溢看着眼前的热闹画面,脸上又露出笑容来。



待到日头西斜,身为东道主的阿卡人开始为夜晚的宴席做最后的准备。男女老少都换上了隆重的哈尼族传统服饰,一起舂糍粑、调蘸酱、烧制烤肉,在竹编的大圆桌上铺开新鲜的芭蕉叶。

哈尼族妇女一般穿着短裙,一是为了农作时走山路方便,另一方面,妇女要捻线纺纱,短裙不会妨碍走路时在腿上搓线的动作。
哈尼族支系众多,他们的服饰也有较大差异,但主要以黑色和藏青色为主,用红、蓝、绿色布料作装饰,另搭配银币、银泡等银饰品和靓丽的禽类羽毛,衣服的布面上还有色彩跳脱的棉线或丝线刺绣作为点缀。
1957年,哈尼族在国家相关机构的推动帮助下,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试验推行。在这之前,哈尼族人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

传统的哈尼族服饰制作时采用植物染料,袖口、衣摆、肩线等位置会绣以各色图案,再搭配色彩鲜艳的绒球、珠子和形状各异的银饰,有着非常独特的民族风格。不过,其装饰细节根据族群居住地的不同,也有较大的变化。
作为哈尼族的支系,阿卡人的文化历史在新的拼音文字大面积推广之前,也只能依赖于代际间的口传身授。除此之外,传统服饰上的刺绣纹样也是民族文化的另类叙述方式。“我看过一些资料,哈尼族的刺绣大概有两千六百年的历史。”书溢的好友二艳是哈尼族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三代传承人,也是专注于哈尼服饰革新的哈倪康帛工作室的负责人,她收集、研究哈尼族的传统服饰多年,能窥见少许被这些彩色丝线捕捉缠绕,并缝补进衣衫间的历史残片。
“阿喀猫”(哈尼语音译)的纹样代表螃蟹的眼睛,是哈尼先祖在感谢山涧中的螃蟹的救命之恩;千折百回的七针花“习拉朵昂”(哈尼语音译),是纪念先人南迁踏过的高山流水,也是告诫后人,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需要珍惜。
“从这些刺绣中可以看到哈尼族人每个阶段文化的不同,比如说,现在的刺绣配色和纹样,就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有很多区别。”二艳还告诉我,和汉族的刺绣不同,哈尼族人刺绣时针随心走,没有固定的模版,绣出的花纹就像是一首记叙的长诗,它们或许是绣娘当下听闻的几段轶事,是她倚靠的窗边自森林间传来的鸟鸣,又抑或是她垂头时飘散的一朵愁绪。
不过,这些辗转千百代的刺绣技艺,目前还是通过以母传女、言传身教的方式来延续。像二艳这样的新一代哈尼族女性,在青少年时期就要离开母亲去县城上学,如果不是自己对传统服饰有着强烈热情,特意钻研,流传自上一辈的技艺很可能就此失传。这也是包括刺绣在内,哈尼族几千年来积累的民族文化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我们没有文字就更容易被外族同化,现在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有几个因素,一个是祖先崇拜,一个是我们的‘父子连名’,还有一个就是火塘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颇为关注的安伞发现,哈尼族人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与被历史遗忘“作战”,而火塘就是串联一切的核心。

阿卡人热情好客,且能歌善舞,特意从大卡老寨赶来的达迁和迷霞唱完敬酒歌后,带领着大家绕着篝火一起舞动。
哈尼族人尚火,将其视为生命的象征,必须保护火种长久不灭。所以在每个传统的哈尼族家庭里都少不了烟火不断的火塘,它不仅具有照明、取暖、烧水、煮饭的日常用途,也是背诵“父子连名”的家谱、传承族规族纪、教授知识文化的重要场所,更是哈尼族人祭拜祖先、与神灵对话的精神空间。火塘,就像是一条穿梭在时间河流中的纽带,维系着哈尼族的生生不息。
阿卡人在接待我们的宴席上也燃起了一团篝火,皮肤黝黑的阿波(哈尼语,意为“阿爷”)将一盅白酒浇在燃烧的木柴上,火光猛然蹿起再炸裂散开,围观的众人也随之热情欢呼起来。
月亮站上屋顶,又跃过橡胶树摇摆的枝头,升至中天。星月交辉,天幕之下,年过古稀的阿波们握着竹酒杯围坐在火堆前,唱起阿卡人的古歌。这些少有人能听懂的曲调,时而高亢,时而低沉,讲述着阿卡人的四季农事、神鬼传说,还有他们崇敬自然,又与其争斗的漫漫岁月,曾在每一座永不熄灭的火塘间流传。
夜色渐深,酒意更浓,老人的歌声也变得悠长,承载着几千载哈尼文明的音调便乘着微醺的晚风,向着亘古不变的远山深处又一次飘荡而去。
摄影 南腊传媒
编辑、策划 杨雨池
采访 Sisi、小怡子、Zhihui
撰文 Sisi
制片 书溢、安伞
文字资料整理 皇大仙
编辑助理 戎杨
特别鸣谢 大卡新
原标题:《去真正的西双版纳,吃一顿雨林杀猪宴》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
Android版
iPhone版
iPad版
- 澎湃新闻微博
- 澎湃新闻公众号

- 澎湃新闻抖音号
- IP SHANGHAI
- SIXTH TON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沪ICP备14003370号
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0299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