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我寄宿在纳米比亚,见证一场跨种族的爱恋 | 三明治
原创 王不羊 三明治

简和赫劳在面对疾病和衰老的过程中,一直据守着爱情,直到晚年都有十分宽广的精神生活。七年前,由于根植于头脑里的种族歧视观念,我对和黑人发展亲密关系心怀恐惧。或许是受他们的鼓励,如今,限制我与全人类相爱的偏见与枷锁已经慢慢消失。
作者 | 王不羊
编辑 | 依蔓、渡水崖
三年前我即将在德国完成硕士学业,但还是想不明白自己将来要做什么。某天看到朋友在留学生群里转发了国际组织的实习项目,我打算试一试。
带着朴素的好奇心,我在公开招募的十六个岗位中,选择了津巴布韦和印度的媒体部门作为意向岗位,最终被津巴布韦录取。转机在此刻出现。该部门负责管理整个南部非洲地区,主管在面试时问我,愿不愿意被下放到国家办公室?与津巴布韦东部接壤的莫桑比克和临靠大西洋海岸的纳米比亚更缺人。新入职场的菜鸟没有细想,点了点头,说可以。

我简单查了查资料,发现纳米比亚的官方语言是英文,而莫桑比克则是葡语区。出于生活便利和易于开展工作的考量,我选择了没有语言门槛的纳米比亚作为最终目的地。
异国搬迁,找房子是头等大事。收到录取通知后不久,我就开始在Facebook上逛小组,发广告,找房源。求房广告一经发出,收件箱里不断涌来陌生人的信息,积极介绍各自房源的地理位置、租金、家具配置和房屋结构等等。除开硬性条件之外,我根据对方Facebook主页的内容、聊天时的措辞、房子的照片和自己的直觉,筛选比较一番之后,心里有了答案。
我要住在简的家里。我跟她说,我喜欢和老年人住在一块儿。
看到简Facebook头像的第一眼,我心里泛起过一丝波澜。
简是一位白人老太太,她给我的第一封私信开门见山,针对我的租房要求一一回应:房子离联合国大楼近,有无线网,和另一位租客共享厨房,独立卫浴(偶尔需要和来访的客人分享),共用洗衣房,没有电视机。除此之外,房前有属于我的小院子、可自由使用泳池和花园,每周会有人来打扫房子、更换床单。“你会和我、以及我年迈的丈夫同住。我们喜欢年轻人环绕身旁的感觉。”她补了一句。
尽管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入住简家,但心里的波澜还未散尽:简的丈夫是黑人。
简的Facebook头像是她和丈夫的自拍合影,两人在镜子前相视一笑。在1966年至1990年期间,纳米比亚被南非接管、统治,也承袭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黑人是白人的帮佣、园丁,是被强制劳动的杂役。白人能吃白面包,而黑人吃棕色的全麦面包。当然黑人也分深黑、褐黑、棕黑、浅黑等等,滑稽的肤色主义,决定了他们在白人统治下的地位等级。
黑白配的故事,似乎没有在主流叙事里被正面提及过。一位在肯尼亚的师姐曾对我说,有很多白人来蒙巴萨的海边猎艳。男女都有,平均年龄在四五十岁左右。他们专雇年轻、迷人的黑人青年陪游。这些年轻人明面上是向导,实质上更像是出租男友或女友,在陪游期间和雇主约会,提供一对一的性服务。他们互相利用。一方在鲜亮的躯体上寻欢作乐,另一方能拿到不菲的小费,供其挥霍享受。这样的故事说多了,流传久了,就变成了唯一的叙事:如果不是有利可图,黑人和白人怎么会在一起?
在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之下,白人与黑人通婚被法律定罪。简和她的丈夫,两个老人的故事,当初是以哪个蓝本展开的呢?

简和赫劳的结婚照
当我准备启程时,新冠疫情的重灾区正从国内往世界各地转移,纳米比亚在2020年3月关闭边境,再无航班通行。大使馆也进入半休业的状态,签证申请不再受理。经过和办公室的协商,我决定先回国远程办公,静候其变。
在等待出行的八个月里,纳米比亚国境逐渐开放,签证官也重现踪迹,然而订好的航班却几度熔断。我几次改签,始终无法成行。简和我一直保持着联系。有好几次我跟她说,要是有人想租这个房间的话,请不要有顾虑,租出去吧。她说好,但那个房间还是保留到了我来的最后一刻。
二零二零年的圣诞节前夕,我在高空中顶着烈日,终于看到了纳米比亚首都温特和克的群山。


刚到温特和克时,城里正经历第二波疫情高潮。
尽管疫情严重,简心里有顾虑,她还是在我到的第一晚,也就是平安夜,叫我一起参加家庭聚餐。她的儿子弗雷迪及新婚妻子、女儿图丽和收养的孙女儿都来了。大家戴着口罩,从盘子里切肉、淋酱、舀沙拉、叉土豆,然后端好各自的餐碟,隔着距离,散坐在客厅的沙发凳上。
他们叙着家常,我在一旁吃着,穿着背心短裤,适应自己在这个家庭里的新角色。挂在圣诞树上的小灯泡抚平了夏夜的燥热。堆放在树下的是家人间互赠的礼物,用彩纸精致地包着,是许多份值得期待的惊喜。简居然也给我准备了礼物。绘有卡通动物的圆盒子里,装着三个橡皮泥质地的解压球。用手捏一捏,还能蹭点儿香味。
入住的第一天,我在房间里发现了一本颇具年代感的小书。书皮上以绿汪汪的水草和湖泊为背景,在湖面上撑浆划船的是穿着制服的军人,有人手里端着枪。他们的表情祥和、平静。这本书装帧普通,像图书馆里保存的、从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文物。我匆匆扫了一眼,没太留心。
后来在跟简闲聊的过程中了解到,她的丈夫赫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过一本自传。
纳米比亚在1990年独立之前被称为西南非洲(South West Africa)。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同盟国战败,西南非洲从德国殖民地版块中脱离。经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授权,隶属于大英帝国的南非接管西南非洲,从此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在两地通行。
为了稳固白人政权,达到人种平衡,南非政府给欧洲的战后难民提供廉价机票,吸引白人前来定居。与此同时,新殖民政府开始将首都温特和克城区内的黑人赶出市中心,迁往市郊的贫民窟卡图图拉。为了最大化地实现种族隔离,城市规划者只在卡图图拉通往市区的路段设了一个出入口。为了防止黑人团结、合力推翻白人政权,当权者不仅将定居在卡图图拉的人们隔绝于城市,也按照部落,严格划分他们的居住区。这样的殖民景观依旧保持至今。
这本自传记录了赫劳的童年回忆、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强制劳动的经历,以及后来加入SWAPO(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现纳米比亚的执政党)为争取国家独立的抗争。
加入SWAPO后,赫劳被抓捕、审讯、关押在罗本岛十八年,最后被释放、流亡英国。以流亡者的身份旅居英国的赫劳和简相识、相爱,走入婚姻。生下第一个孩子图丽之后,简继续工作,而赫劳因为工作许可申请没有得到批准,在家履行父职,照顾图丽。
在此期间,他决定把自己的前半生写下来。

摄于纳米比亚独立纪念博物馆,
感谢舍友徐慧提供照片
我突然想到了房间里的那本绿皮书。我问简:我房间里是不是有这本自传?她说是的。每次有新租客入住时,她都会拿出一册放在房里,作为见面礼。
回房之后,我捧起书,急切地想要了解赫劳身后的传奇故事。我一边读着他开篇写下自己的部落童年生活、有祈雨能力的“雨神”父亲、在深林里与狮子的四目相视,一边想到了他再也无法自如表达的身体。赫劳在五年前中风,不仅身体行动不便,出入需要轮椅,而且语言能力也受损,跟人交谈时需要简在旁协助、转译。
他们的夜晚常常这样度过:简深陷在沙发里,端着碟子里的晚餐,打量着电视上的厨艺大赛,倦意散落一旁。没过多久,手边的呼叫铃传来一阵悦耳的抒情小调,她长叹一声,身子往沙发里缩了缩。铃声不断响起,简一边急切地对着回廊深处的房间喊着“我来了”,一边用双手撑着膝盖起身,骨头缝里溢出一丝呻吟。
房里的赫劳快九十岁了。两次中风之后,他的舌头和四肢已经不听使唤。身边没人时,手心里的呼应铃就是求助装置,只要他轻轻一按,一段轻快、机械的钢琴声会从房里响起,穿过回廊和前厅,和简随身携带的另一只提示铃互相呼应。
夜晚是简最放松的时候,尽管她需要时不时地在前厅和房间穿梭,帮赫劳起床夜尿。她不再端坐于藤椅之上,任由脊椎贴向软榻的沙发靠背,坐骨越陷越深。眼前的电视节目也从白天不间断的新闻变成了真人秀。厨子、吹玻璃的工匠、准备大搞一番家装改造的夫妻,轮番上阵,慢慢地将堆放一旁的倦意扫进摇篮里,哄她入睡。

简之后也多次邀请我参加她们的家庭聚会,有周末例行的聚餐、赫劳从罗本岛被释放的纪念日、简和赫劳的生日庆祝、感恩节等等。我有时也会和简一起备菜,在厨房里煎蒸烹煮,包点饺子,炒个豆腐,磨碗枣泥,炖锅牛肉,给饭里加些中式口味。蘸饺子的酱油碟尤其受这一家人喜欢,她们总笑着催着我开工作坊,传授传授秘方。
那段时间,我总会在晚上和简一起看电视,期待和她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坐在同一张沙发上,身隔半米宽的距离。电视里播着厨艺大赛,工匠们在吹着玻璃,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白天发生的事情。
我偶尔会因为工作原因去电视台接受直播采访,播出时间在清晨六点左右。去接受采访时,我因为怕丑,除了男朋友之外,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简和赫劳。没想到,他俩赶上了直播。
每天早上六点左右,夫妻俩虽未起床,但会打开电视,倚在床头收看纳米比亚广播公司的晨间新闻。那天正好看到了我身着臃肿的羽绒服,戴着渔夫帽和口罩,接受采访的生涩模样。我习惯性地为自己的英语表达不自信,而简在我回家后高声庆祝,夸我作为非母语者,思路清晰,言之有物。坐在轮椅上的赫劳也握起拳头,为我喝彩,脸上爬满了雀跃和欢呼。
我也很快发现,身边的人都能和简与赫劳一家人扯上关系。
在国内申请签证时,签证官利用职务便利,托我带了一些衣物、手机和口罩回纳米比亚给他的老婆孩子。抵达纳米比亚之后,有个女人联系了我,自称是签证官的亲戚,要来取件。我们约好了在我家门口见面。她接过我手里的塑料袋之后,朝屋里打量了几眼,问:这里住的是施图维特一家吗?施图威特是赫劳的姓氏。我当时还没太记住这串名字,想了一会儿,说:好像是的。她说:啊,我认识他们,让我上去打个招呼吧。果然是人人知晓的英雄人物啊,我心里想着,对签证官占我便宜的不忿也淡了一些。
新年伊始,在圣诞元旦假期中沉睡的小城渐渐苏醒过来,城里唯一的一家瑜伽馆也重新开张了。简告诉我,瑜伽馆的主理人劳拉是女儿图丽的朋友,两人都曾活跃在剧院里。劳拉是电影和话剧舞台上的主角和宠儿,图丽是知名的舞蹈家,主演过多部芭蕾和现代舞剧。慢慢地,我开始通过瑜伽认识了更多的人,她们都与简和赫劳有这样或那样的渊源。

图丽在剧场里
在一次瑜伽讲座课上,劳拉请来了恩达普瓦。恩达普瓦是一位黑人女性,和简一起在当地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权益组织——纳米比亚姐妹(Sister Namibia)共事。她跟我们聊了聊瑜伽应有的种族包容、性别包容和阶级包容。
简和赫劳都是女性主义者。他们和图丽一起在二零二零年十月的终止一切(Shut It All Down)女权主义运动中上街游行。全城罢工,一大批年轻人占据街头,对香农-瓦瑟夫的死表达愤慨。停止性别暴力的呼声回荡在城里的主干道上,被无数镜头捕捉,登载上报,传入执法者的耳中。在一众青年男女里,简和赫劳显得格外耀眼。

我在瑜伽馆认识的纳米比亚大学老师吉尔,也正在跟进赫劳的自传再版。吉尔告诉我,简要给新版的书写一篇后记,聊一聊这三十年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说,温特和克很小,没有谁可以守住秘密。是啊,温特和克很小,我认识的人都认识简和赫劳。

我们家离机场四十公里,位于城市中轴线的主干道旁。从机场方向向西驶出三十分钟之后,干瘪、枯黄的稀树草原渐渐消失,逐渐过渡到依山而建的城市景观。这时就差不多到家了。
城里没有高楼大厦,多是独栋楼房,我家也不例外。刚到这儿无事可做时,我偶尔会爬上屋顶,看看夕阳,喂喂蚊子,眼前一片开阔。
我的房间是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新增的一部分。简和赫劳在十几年前搬进来时,把空荡的偏院改建成了一间小厨房、杂物库和卧室。通往前院的卧室门前还保留着偏院的一隅。
属于我的卫浴空间与厨房背靠背,也与简和赫劳的房间隔着回廊相望。每天早上起床洗漱时,能听到半阖的房门里传来晨间新闻的声音。从纳米比亚广播公司,到Sky News、CNN和BBC,一整天下来,电视上会滚动播放不同频道的国际国内新闻。去年一月美国国会暴乱时,简把我从房里叫了出来,和她一起在沙发上看直播。她怕我错过见证历史的机会。他们有时比我还更快关注到国内的疫情发展、洪灾和在气候峰会上的立场和发言。
简说,赫劳身体还硬朗时,有新闻囤积癖,经常把报纸丢得满屋都是。床底下,抽屉里,餐桌上,时不时会冒出老旧过时的报纸。这是他在罗本岛坐牢时养成的习惯。除了圣经之外,罗本岛上的政治犯不被允许读书,读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和普通囚犯做交易、打暗号、贪婪地收集和隐藏书报,躲避狱卒的搜查。他们渴望了解游击队同伴们的近况,想要知道纳米比亚寻求独立的议程在联合国的进展,以及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大事。他们不想成为一座孤岛。

1990年3月21日,
赫劳和女儿图丽在温特和克街头见证纳米比亚独立
回廊的墙上挂满了他们一家的照片,紧挨着彼此。回廊的这一头住着简和赫劳,另一头是前厅。前厅既是会客室、电视厅,也是简给赫劳读书念报的地方。跟回廊上随意挂着的生活照不同,厅里装点了许多有仪式感和纪念意义的相片。一家人的艺术写真、孩子们的结婚照、图丽演出的剧照和影像,以及一幅罗本岛的鸟瞰图。
前厅连着简的主厨房和工作室,整片区域正好和我的个人空间一分为二,为疫情期间的相处提供了隔断和防护的便利。
前段时间入夏,温特和克下了场大雨,几分钟内大雨变成冰雹,一颗颗白色的子弹往屋顶噼里啪啦地砸。我关了窗,耳朵里依旧灌满了从四面八方传来的燥热鼓点。外边一片疾速汹涌的白,不一会儿就完全盖住了夏天的生机。院子里的花草被一顿毒打,折断了腰。
简和赫劳出去给家里的猫买项圈了。我赤着脚走到舍友的房间门口,想叫她一起看冰雹。敲了敲门,顶着冰雹的噼啪声叫了她几下,没反应。抬步往回走时,我才注意到整个房子都在漏水。简的主厨房在漏水,我们的小厨房在漏水,紧邻小厨房的杂物库直接变成了水帘洞。抬头一看,杂物库的屋顶被冰雹砸出好多孔,头顶的瓦片像流涎一样往下注水,脚下的地毯湿了一片。回房一看,我的床边也长出了小池塘。

我赶紧给简发消息:简,不好了,刚下了一场冰雹,现在家里到处都在漏水。
没过几分钟简给我回拨了电话:杨,你能不能把桶都拎出来,放在漏水的地方接水。我们马上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简一直看着小仓库里的纸盒子发愁。
纸盒子里堆满了对赫劳的采访和报道、他被关进罗本岛之前的庭审记录、在英国流亡期间的演讲、从政的资料,Swapo背叛者卡斯特罗的采访CD、跟简的通信、在朋友葬礼上的悼词、孩子们写给他的卡片等等。尽管简在这几年里不停地整理这些文件,给它们归类,建了一个小小的档案室,但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新的文件从各个角落里长出来,一茬一茬的,总也收拾不完。整理好的、没整理好的文件都装进了一个个贴好标签的纸盒子里,像一块块小积木,码在仓库的边边角角旁。
这次房顶被砸穿,雨水不仅顺着凿穿的孔倾泻而入,而且还攀附着墙缘,一点一滴地渗漏。仓库里有很多报纸、杂志和纸质文件都被浸湿了,那两张采访CD的塑料壳上也积着雨水。冰雹下了二十分钟之后就停了,但外面还是时重时缓地下着雨,天气预报说晚上会有雷阵雨。我们搬来一把小梯子,踩上去,想用一只黄色的橡胶手套把屋顶的洞堵住,不奏效。我们又找来一坨橡皮泥,还是没用,小水珠沿着堵塞物的曲线自由通行,随着重力下坠。
把被水打湿的文件抢救出来,摊开在房间的地板上晾干之后,简看着满屋的箱子,不知该作何打算。仓库里的箱子太多了,搬进搬出是个体力活儿。要是不搬的话,所有的文件可能会在晚上的雷阵雨攻势下被损坏。城里有很多人家的屋顶都被砸坏了,修屋顶的工人忙不过来,要过几天才能到家里来看看情况。
我们在前厅坐下,想了想对策,顺便聊了聊七年前全家去安哥拉寻根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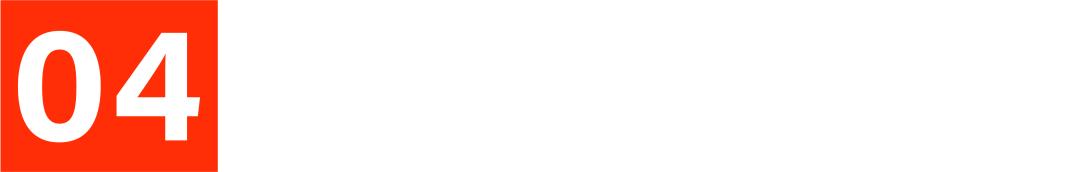
七年前,赫劳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全家一起去了安哥拉为他寻根。
赫劳出生在安哥拉和纳米比亚接壤的边境村落里,父亲是当地的“雨神(rain king)”。他是“雨神”二十二个孩子中的第十九个孩子。四岁时,赫劳被皈依天主教的妈妈带走,离开了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跟母系家族一起生活。六岁时,赫劳的父亲去世,他去参加了葬礼,从此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了。
夫妻俩早就萌发了寻根之旅的想法,想找到他父亲的坟墓。可惜安哥拉前几年一直深陷内战,外人难以安全出入。再加上记忆久远,村子又在难以通行的山区森林里,没有地图的话根本不知身在何方。此外,赫劳的老家又是战时的地雷区,那一片通行的区域都埋满了地雷,大家更是不敢贸然前行。
在他八十岁的那一年,刚好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他们有位朋友是地质学家,根据赫劳的描述和村落的大概位置,绘制了一张地图和通行路线,供他们参考导航。第二,他们女儿的另一位朋友刚好跟排雷公司有合作,跟他们再三保证赫劳老家的那片区域已经排雷完毕,没有通行的风险。就这样,他们夫妻俩,带上二十出头的儿子弗雷迪和女儿图丽,以及从小跟他们生活长大的侄子西荷珀,还有一个摄影师朋友,上路了。摄影师朋友本来是想全程记录他们的寻根之旅,但由于在边境时被阻拦入境,只能临时退出。他将相机的使用方法告诉了弗雷迪,希望借由他来完成简单的拍摄。
找到父亲的坟墓时,赫劳还找到了他唯一在世的弟弟里盘格尼,“雨神”的第二十三个孩子,此前不为他所知的幼子。里盘格尼是“雨神”的继承人,曾经和图丽说过要把祈雨的技法和要诀都教给她。不过他在兄弟相认一个月之后就去世了,两人只留下一张合影。
也是在这次冰雹事件前不久,里盘格尼的女儿从安哥拉长途跋涉,来到温特和克看望身体抱恙的赫劳。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她不讲英文,只懂奥万博语(赫劳的部落语言)和葡萄牙语,通过赫劳的护工,也是侄女玛丽亚的翻译和帮助,才能和简交流。这是赫劳和遥远的故乡仅有的联系了。

七年前在村子里和家人合照
八月份的一天,我收到了简的信息。她在聊天框里发了一张邀请函过来。邀请函正中间是赫劳的照片,他坐在沙发上,盖着毯子,微笑着朝镜头挥手。右上方是一个大大的88——赫劳要满八十八岁了。
过去两年,简和大多数老人一样,活在疫情的阴影下。她总是为赫劳的身体状况担忧。家里严格限制了所有聚会的规模,不仅是各自的生日,连儿女的婚礼也办得十分简单。这次聚会是对之前所有遗憾的弥补,既为悼念逝者,也为生命举杯。
那天我到得比较晚。从露台走近前厅时,发现房子被气球、蛋糕和气泡酒装点,屋里满满当当地站了不少人。角落里有一支小乐队,正奏着赫劳最喜欢的歌,The Wind of Change。仪式开始后不久,一位奥万博族的老婆婆慢慢走向赫劳,握着他的手祷告。她嘴里念着奥万博语,闭着眼睛,半是吟唱,半是念颂,庄重而神圣。屋子里虽有一半的人听不懂,但大家都随着她的音调起伏慢慢红了眼眶。
图丽和弗雷迪站在人群中间,念了一段写给父亲的话。其中有一句,是关于原谅:他原谅背叛者,原谅奴役者,原谅罗本岛上的狱卒和警官,但没有原谅体制不公。他们一直在抗争。作为纳米比亚独立后的自由一代,图丽承袭了父母的工作和使命,在结束舞蹈职业生涯之后,她开始为修复种族隔离的伤痕而行动,编写了许多与种族议题相关的课程大纲,在世界各地组织研讨会与工作坊。
我坐在地上,看着眼前的一切,回想着这一家人的故事。因为他们,我对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有了亲切感,它不再是冷冰冰的宏大叙事,或是遥远的、其他人的回音。我作为外来者的视角不再受限,而是和曾经发生的一切产生联结,生命与辽阔、厚重的曾经、现在和未来交汇。
那些历史和记忆都藏在仓库的纸盒子里,简不想冒任何风险失去它们。尽管冰雹过后,雷阵雨没有在晚上如约而至,简还是在儿子弗雷迪的帮助下,一趟趟地把所有箱子都运了出来,存放在空置的另一个房间。在那些箱子中,只有一个属于她自己。她和赫劳的情书、关于自己和朋友的剪报、以及父母和孩子的物件。
简在脸书上写过这么一段话:“大多数时候,我都会大声读书给赫劳听。这是我们目前的阅读书目。读哪本书取决于他的心情,和朗读者的心情。”
简和赫劳在面对疾病和衰老的过程中,一直据守着爱情,直到晚年都有十分宽广的精神生活。七年前,由于根植于头脑里的种族歧视观念,我对和黑人发展亲密关系心怀恐惧。或许是受他们的鼓励,如今,限制我与全人类相爱的偏见与枷锁已经慢慢消失。




原标题:《我寄宿在纳米比亚,见证一场跨种族的爱恋 |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
Android版
iPhone版
iPad版
- 澎湃新闻微博
- 澎湃新闻公众号

- 澎湃新闻抖音号
- IP SHANGHAI
- SIXTH TON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沪ICP备14003370号
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0299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